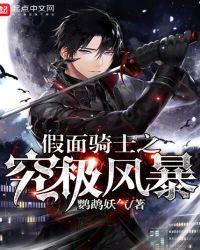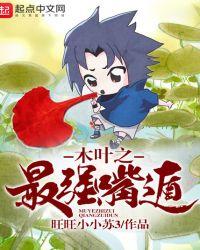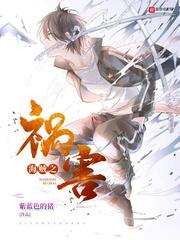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状元郎 > 第二百六十六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2页)
第二百六十六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2页)
眼看前途未卜,苏录却依旧从容。他深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科举之路已毕,而仕途之险,远胜考场十倍。
某夜,他独自登临京郊万寿山,俯瞰灯火万家。凉风吹动衣袍,他仰望星空,喃喃自语:“我求的从来不是功名,而是能让这天下少些苦难,多些清明。若为此需忍辱负重,那便忍之;若为此需步步为营,那便行之。”
身后脚步轻响,却是好友赵元澄悄然到来。
“你果然在这儿。”赵元澄递上一件披风,“听说你要被外放江西?那边瘴疠之地,民生困苦,可不是好差事。”
苏录接过披风披上,笑道:“正因如此,才值得一去。若只挑膏腴之地做官,岂非与那些钻营之徒无异?”
赵元澄叹道:“你倒是看得开。可你可知,张孚敬之所以执意打压你,不仅因你受杨阁老赏识,更因为你策论中提及‘清丈田亩’一事,触动了多少权贵的利益?江南豪族、勋戚之家,哪个不是靠隐匿田产逃避赋税?你这一招,等于断人财路啊。”
苏录闻言,面色不变,只道:“我知道。但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真话。否则,我对得起十年苦读?对得起那些饿死在路边的百姓?”
赵元澄默然良久,终是拱手道:“好兄弟,我不劝你退缩了。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两人并肩伫立山顶,遥望东方微明。
黎明将至,天地渐亮。
数日后,诏书下达:新科状元苏录,授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知县,即日赴任。
临行前,母亲含泪送别,叮嘱道:“儿啊,做官不易,但无论身处何地,都要记得初心。”
苏录跪地叩首,郑重应道:“儿谨记。”
马车驶出京城,尘土飞扬。回望巍峨宫阙,他心中并无眷恋,唯有坚定。
他知道,真正的答卷,此刻才刚刚开始书写。
一路南下,沿途所见令他心惊。黄河泛滥之后,灾民流徙,沿路乞讨者络绎不绝。官府设粥棚救济,然杯水车薪,饿殍仍随处可见。更有地方豪强趁机贱买田地,逼迫农民卖身为奴。
至丰城境内,情况稍好,然赋税沉重,百姓负担极重。前任知县贪墨成性,亏空库银数千两,民怨沸腾。苏录甫一到任,便下令查封账册,彻查历年收支。
县丞周文达原以为这位年轻状元不过是来镀金走个过场,必定不懂实务,便于操控。岂料苏录虽出身寒门,却自幼随父习算学,精通钱谷出入,仅三天便查出十余处账目漏洞,当场怒斥周文达:“尔身为佐贰,不思辅佐牧民,反助纣为虐,罪不容赦!”
随即上报巡抚,请革其职。
此举震动全县,胥吏为之震慑,百姓拍手称快。
接着,他发布告示,减免受灾农户今年赋税三成,并开放常平仓赈济贫民。同时招募工匠,修缮城防、疏浚河道,以工代赈,安置流民。
短短一月,丰城气象为之一新。
有人问他:“大人如此作为,不怕得罪上司?”
苏录答:“我头顶是青天,脚下是黎民,中间是良心。只要问心无愧,何惧他人言语?”
话传至巡抚耳中,巡抚冷笑:“年少气盛,不知深浅。”
然不久之后,一道密令自京城发出:责令江西布政使司彻查丰城县赋税改革是否“逾制扰民”。
显然,有人不愿看到一个小小知县掀起波澜。
面对压力,苏录并未退缩。他整理所有文书档案,连同百姓联名请愿书一同封呈,附奏折一封,详述施政理念与成效,直言:“所谓扰民者,实乃触犯豪强私利也。若因畏惧权势而弃民不顾,则非臣之所愿为。”
奏折递入通政司,辗转送达御前。
皇帝再次展读苏录文字,沉吟良久,忽然问道:“此人,可是前年殿试那个写‘振作人心’的苏录?”
身边太监连忙答道:“正是。”
皇帝点头:“此人骨鲠可用。传旨,嘉奖其勤政爱民之举,赐绢帛五十匹,以示鼓励。”
圣旨抵达丰城当日,全城百姓夹道迎接,欢呼声震天动地。
而京城之中,张孚敬闻讯,脸色铁青。
“此子不除,必成大患!”他咬牙切齿道。
可他也明白,如今圣眷已加,轻易动不得了。
一场风暴暂时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序幕。
苏录站在县衙门前,望着阳光洒满街巷,孩童嬉戏,老人晒粮,炊烟袅袅升起。
他轻轻抚摸腰间那枚新铸的县令印信,低声说道:“这才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