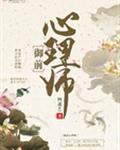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明王朝1627 > 第83章 天下之大弊莫过于殆政(第3页)
第83章 天下之大弊莫过于殆政(第3页)
答:“是。”
问:“那难道,就无一人停马驻足,问一问这其中缘故吗?”
老者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看举人,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有。”
……
朱由检猛地合上了答卷,呆怔半晌,一语不发。
大殿之中,死一般的寂静。
高时明见他神色有异,悄悄上前一步,低声问道:“陛下,可是有何不妥?是否要将写此文之人,叫上前来奏对?”
朱由检缓缓地摇了摇头。
这上面的例子,纵使有所隐瞒或疏漏——例如权贵、官宦诡寄应该也是造成当地赋税陷入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但别人也确实是赤心诚意地把最糟糕、最真实的情况全盘托付了。
他如果这样把人拎出来当众标榜追问,实在有点“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的意思了。
他看了一眼封面上所写的名字,将几人的姓名牢牢记在心中,打算后面再多加关注。
“辽东发赏小组:行人袁继咸,中书舍人胡志藩,锦衣卫王世德、田有光、王铿才、李季有、吴继嗣。”
终于,朱由检缓缓站起身来,一步步走下台阶,看着殿中那一双双炽热、紧张、又充满着期盼的眼睛。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终于缓缓开口。
“今日读诸位之文章,就如拨云见雾,朕到今日才知,这天下之情弊,果如同重檐迭峦,实非一日可撼。”
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
殿中众人闻言,一时均有些失望。
不少人视今日召对为登天之阶,此刻听闻皇帝这般说,只觉得心头一凉,那股子热切顿时消散了大半。
更有一些先前言辞激烈之人,热血退却之后,想起自己所书的大胆言论,甚至有些后怕与纠结起来。
朱由检将众人的神情尽收眼底,话锋却猛地一转。
“然,天下事,做则成,不做则亡!”
他也不迈步,就站在台阶之上,目光灼灼,扫视众人。
“今日搬一山,明日搬一山,则太行、王屋不可阻其志;今朝挖一渠,明朝挖一渠,则江河亦可改其道!”
他双手虚张,仿佛要将整个大殿都揽入怀中。
“但如今,却要从何事做起呢?”
朱由检语气一顿,阶下众人略微的骚动,瞬间平复下来,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着他的下一句话。
“古语有云: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朕欲行天下之治,则必先通上下之情!”
“诸位此去九边颁赏,朕特地定了名单,以本籍贯之人,往本籍贯之地发赏。”
他话到此处,突然止住不讲,转头去看高时明,问道:
“高时明,为何本朝发赏旧例,总以他籍之人行之?”
高时明躬身道:“回陛下,此乃为防本地籍贯之人,与当地官吏军将勾结,滋生情弊。”
朱由检点点头,回过头看向众人,下一句开口的话却让人毛骨悚然。
“然,他籍之人,便不会有情弊吗?”
阶下众人一时更是骚然,过往有过颁赏经验的行人之中,更是多数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朱由检那灼热的目光。
朱由检幽幽地叹了口气。
“也会有的。”
“这大明俸禄低薄,进士登科,甚至要举债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