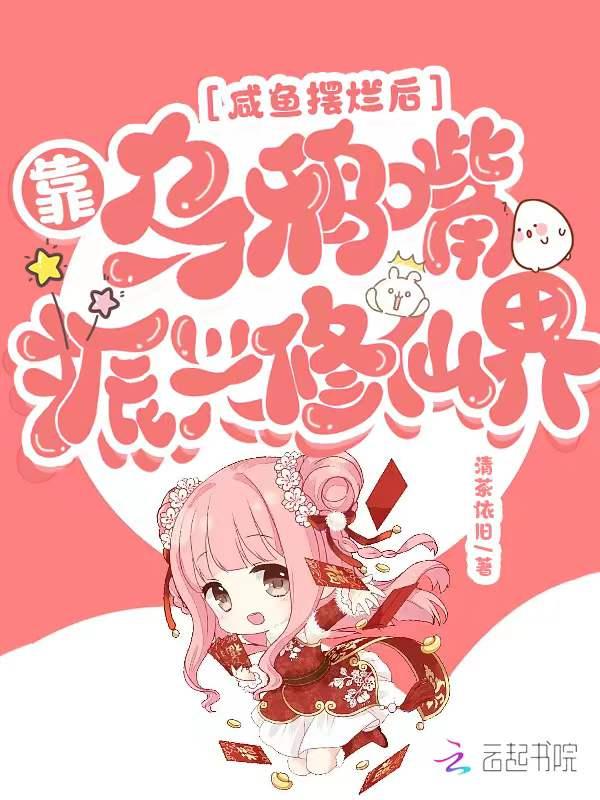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渡平城 > 6070(第28页)
6070(第28页)
对他而言,都是死局。
“阿娘”
“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郑氏宽慰着他,温柔地替他拭泪,自己却不知什么时候也蓄满了泪,“都是成家的人了,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了。”
眼前的拓跋琅青葱俊逸,同拓跋允长得格外相像,眉眼间又带着母妃的柔和。
这是她花了许多心血养出来的好孩子,她亲手教他读书、写字,亲眼看着他娶妻、生子。
在冯芷君那,居然只能做争权夺利的刀!
她怎能不恨!
“琅儿,阿娘只问你一句,”郑氏轻抚着拓跋琅的面庞,音量很轻:“倘若冯后要立你做傀儡,你应是不应?”
傀儡也是天子之位,泽被子嗣,待熬走了冯芷君,便是一国之主。
但他若应了,便是要拉着整个大魏分崩离析。
“”拓跋琅垂头良久,复又望向郑氏,面目坚毅,匝地有声道:
“孩儿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
郑氏望着拓跋琅的脸,终于笑了出来。
阿郎、秀娘,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们的孩儿、我的孩儿,他秉性纯良,傲骨铮铮。
“你父王、母妃泉下有知,会为你感到欣慰的。”郑氏抱着拓跋琅的头,“去吧,去好好看看你的妻儿,勿要担心阿娘。”
“阿娘”
拓跋琅还想说什么,郑氏却止住了他,拍着他的手,“你的妻儿比阿娘更需要你。”
“孩儿不孝。”拓跋琅听话,站起,再度下跪,朝郑氏行大礼叩拜,“不能以此身侍奉阿娘。”
郑氏没有再拦着他,看着他叩首行礼,深深互望,而后瞧着他消失在门外。
她替拓跋允守了十余年的寡,一己之力撑起整个任城王府,再柔软的心,也变得坚韧了起来。
诚然她位卑,不能同冯芷君对垒相抗,可她也不是木偶,任人摆布!
“去信洛阳,送至京兆郡公手上,将世子入宫之事原原本本禀与她。”
冯初
拓跋允在时,私下多次赞她风骨卓绝,有名臣风范。
也只能赌一赌,当年那个来任城王府索要文书,拓跋允口中与他惺惺相惜之人,是否属真。
“你们动作都快点,还不把这些恼人的知了粘下来,当心惹恼了太皇太后!”
安昌殿内,宫婢寺人取了竹竿,忙着粘知了,闻妙观此言,手上动作更快了些。
妙观深深叹息,太皇太后心中除开不满拓跋聿,当还是对冯初有些寒心。
过去这般久,冯初不曾往宫中送入一封书信陈明战事,亦不曾对陛下出走洛阳一事言表一字。
这落在冯芷君眼里,无异于已经站在了拓跋聿一边。
妙观不敢品评冯初与冯芷君孰对孰错,只是唏嘘,从前冯初那般敬慕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更是花了心思为她铺平仕途。
现如今,却落得个针锋相对的结果。
她站在佛堂门前,踟蹰片刻,才缓缓推开了那扇雕着莲纹的木门。
冯芷君敲着木鱼的手不曾停歇,待念完这一段经文,才缓缓停住。
“启禀太皇太后,广平王拓跋宪于狱中请见太皇太后。”
“他终于肯松口了?”
冯芷君紧抓着手间白菩提珠,垂眸间,凝着案上铜香炉,不知在想着些什么。
“是。”
冯芷君握着木槌的手放了下来,妙观会意,立马上前,将她扶起身来。
“你先出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