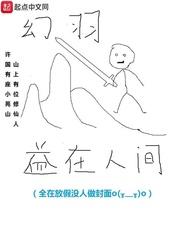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为你织梦 > 末日丧尸异能世界 1(第7页)
末日丧尸异能世界 1(第7页)
他松开树枝,任脚下的残肢滚落屋顶。
三只III级立即俯身,争抢那截焦黑胳膊,牙齿碰撞,像铁钉敲铁盆。
夕阳把它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影子交织在一起,像一张网,网里网外,都是猎物。
缄语者站起身,兜帽被风掀起一角,露出苍白下颌。
他伸了个懒腰,动作懒散,却带着猫科动物蓄势的弧度。
“去吧,”他对脚下的怪物轻声说,“去把热闹闹大一点。”
“我还想在夜里,听到更多人心的裂缝
——咔啦,咔啦。”
声音落下,他转身,脚尖一点铁皮,人影倏地滑下屋檐,像一滴墨坠入暮色。
三只III级捧着残肢,循着他消失的方向,低吼着追去。
远处,最后一缕阳光被地平线吞掉。
保护罩外,真正的黑夜即将来临——
而黑市的老鼠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探出洞口,
舔舔干裂的唇,
去翻找新的裂缝,新的油,新的声音。
-----
蚁城入夜,灯带自动降到“安息模式”,一条冷白被切成三段,中段完全熄灭,只在地面贴出萤火虫似的光斑。
换气扇的嗡声也低了半格,像巨兽把脑袋塞进爪子,开始打盹。
通道深处偶有巡夜脚步,铁底敲在格栅上,声音被潮气泡软,再撞到壁面,只剩闷闷的“嗒——嗒”,像心脏隔着厚肉跳。
监控室藏在第四层腹心,外墙是整块浇注的混凝土,门缝嵌了铅条,隔音也隔振。
里面只开一盏台灯,铁皮灯罩锈了边,灯光被裁成四方,像一块被压平的月,静静铺在图纸上。
叶白岑伏在案前,短发别到耳后,发梢沾了一点铅笔灰。
她握着削得极尖的2H铅笔,线条落得很轻,几乎听不见沙沙声。
每画一道防御墙,就在右下角添一个小小刻度——那是她自己的密码,代表“如果失守,这里能拖几分钟”。
城市被那些线切成安全与危险,她的心也被切成“能说”和“永不能说”。
门轴忽然发出极轻的“吱”——比换气扇还低一分。
韩屿的影子先投了进来,落在图纸上,像一块石头落进静水,把月影撞得晃动。
叶白岑没抬头,只把铅笔翻个面,用橡皮那头点在他的影子上,像按掉一个多余的心跳。
随后她才抬眼,目光穿过灯光边缘,与他对视一瞬,又落回图纸。
笔尖继续走,线条没断,呼吸也没乱。
-----
世界还在漏:
月亮依旧红,只是没人再抬头。
人们低头,
看裂缝、看枪口、看脚下的灯带。
裂缝在长大,枪口在发烫,灯带在老化。
故事从这里开始慢慢爬,像一株没有名字的草,先扎根,再顶开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