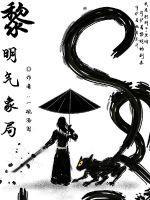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著情为篇 > 相信文字(第2页)
相信文字(第2页)
“既然都走到了这个步骤,那么李婶可以选择继续骂这家店,而且不要单单拘泥于做饭早餐,甚至可以上升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店怎么来的,谁知道你饭里是不是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怎么?一把年纪了,想起来开店了?是为了治你那个瘸腿老公啊?’诸如此类的。”
周义之皱了皱眉:“会不会不太好啊?怎么还上升到人身攻击,撕人家苦难皮子了?”
方秉尘帮着徐照月答了话:“从文字的角度上来说,这并单单不是一种扒开人经历的苦难这么简单,而是李婶的性格只能支持她说出这样的话,只能支持她做出这样的事,刚刚不就说了吗?你要是想把一个人塑造好,你首先要贴合她的人格,贴合她的性格,而不是把自己的道德感放在这一切之前,你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你,虽然无论是哪一个角色,都会在无意中,以正面或侧面显露出你自己的情,你自己的志,你自己的思,表达出你自己的观念,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一切的前提都是:你笔下的人物,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
周义之算是明白了这么一回事,示意那两位继续往下说,徐照月又自然的将话头子顺了过去:“是的,而且一个不够理性,文化程度或者人文程度更低的人,情绪上头的时候一定会口不择言,但我们也不能单单靠文化程度去定夺一个人,还包括起冲突或者影响情绪的这件事情,对于被影响的这一方来说,是否足够重要,影响是否足够大,是否让她放弃了理智,甚至于不能说是放弃了理智,而是说情绪所裹挟。”
“我们来继续说,那既然李婶都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心中的愤恨和不满是否会持续增加呢?那她是否会耍一些阴招呢?如果她足够大胆,她可能会去在大锅饭里下泻药,以此来败坏那家店的名声,如果她没有那么大胆,甚至于,无论是她自己心生一计,还是另有其人给她出招,是我们就可以让李婶假意要去王婶的店里好好尝尝究竟是个什么滋味,于是她在自己的饭里下了泻药或者她归根结底还是不忍心伤害自己,是个贪财霸道又惜命的人,她可以在饮食的过程中,或者吃完以后去装装昏倒,装一装腹痛不已的样子,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太俗套了,就是你如果串联前后内容来看,你会发现你的情绪一定会被吊着往上走,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种被气笑了的感觉,而且有时候俗套并不是俗了,而是有一部分人或者在这种场景之下,普遍人们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样的行动。”
“自然你就会觉得俗套了,这是一种生活之中,所谓的约定俗成,也是安全隐患上所对标的最大问题,这是基于常识所创造出来的故事情节,这也恰恰说明了食品安全以及饮食安全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关键,我们暂且不提如何写才能不俗套,首先先要明确一个大点,那就是:不要害怕自己的剧情俗套化。”
“在文学意义中,并没有绝对的俗套,一方面是文学,一定程度会对标生活,另一方面,文学发展至今已经足够浩大,足够广博,所以必然会有同质化的内容,相同化的情节,但这和抄袭或借鉴是两码事情,就好像在古诗文中,我们提到牧童总是能想到吹笛,我们提到莲花总是能想到清净,这些种种都在反映着这些所谓同质化的俗套内容无外乎有三大影响因素。”
“一、生活经验或习惯的固定性。
二、文学广博所带来的难以绝对创新。
三、我们读的书虽然很难说足够多,一定在读书的过程中积累出了一种语感,这是一种文字的感觉,你的感觉会自动把这个空隙给补上,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意象美,也是一种,无数文人在千百年之中的碰撞。
”
或者说,有情人。
当你模糊地触露到文字感情边缘的那一刻,你就注定了会和文字相伴一生,注定了你是个天底下难得的有情人。
叙一庭对于这些话有了自己的一些懵懂理解,心里思忖了一阵,再度将话题绕了回去:“所以节奏也是这个道理,对吗?比如我们继续说回李婶,几度三番不成,她可能就会走上极端的路子,哪怕她的行为上不极端,在言谈上也一定会有之扩大,比如起初她可能还在叫嚣着王婶的饭店不怎么好,并没有什么吃头,哪里比得上自己家的,接着后面可以造谣,说吃了那些饭容易肚子疼,甚至吃了对脑袋不好,然后再把话语上升到挣这些钱是为了补给王婶自家的苦难,嫁了个瘸腿的老公,也是断人财路的报应,甚至于到最后还可以去联合着一众早餐店的人,嚷着嚣张说都是因为有了王婶这个人,才害的大家都没生意,自己当然没什么事情,自己少挣一点就少挣一点了,但是千千万万个老板们总归都要吃饭的吧?那些顾客全都跑到王婶儿她们家去,难道是想着让大家全都在外面要饭吃?”
甜梓应道:“好一招借刀杀人!明眼的应该都能看出来吧?”
“是啊,不是聋子的都能听出来,她这话到底什么意思,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商家被这些情绪所裹挟,场景就热闹起来了,从两个人之间的争执写到了整体的局面上,这样人物就不会单一了。”
“而且一个好的人物是不能面具化的,这里的好并不是说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正派的、正向的人,”方秉尘又道:“而是说你要把这个人活起来,比如我们前面说王婶有一个瘸腿老公,我们还可以给李婶设置一个急着攒治病钱的人物设定,这些年来挣的钱,无非就是为了去给小孩治病,在这一层面上,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德绑架的成分,所以这就会再度把场面分成两大波,起码两大波。”
“一部分人呢,动了恻隐之心,另一部分人呢?则是觉得那你不如好好做馒头,做早餐,只要饭香,食客自然会来,这里搅和别人的事情算什么?”
徐照月再度接了话:“是啊,那么,当这些意见无数次产生冲突的时候,这是笔下观客的想法,一定也会有着一部分读者的想法,虽然对于作者来说,有人会觉得简直就是左右脑互搏,但你既然想写好,你首先就要允许这一切的存在,而且平时的观察也是很重要的,写作想写得好,写得生动,写得巧,单单是读书那么简单,读书归根结底也是在读人,读笔下的这些人、读写出这本书的这个人,读那些情感、那些思考、至于是情怀或者意志。”
“节奏自然也是这么慢慢拉上去的,把情感的拉扯提升上去,并不单单是要提升笔下人物的情感拉扯,更是要把读者的情绪给拉扯起来,刚刚举的例子虽然死板老套,但是结构清晰,一目了然。”
周义之点了点头,自己的黑色眼镜框扶了扶:“是这么一回事,而且节奏并没有绝对的快或者慢,可能同样一种节奏风格,对于不同的角色来说,适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一个急性子或者在某件事情上很着急的人,他可能并不会在家里面弯腰穿鞋,将鞋带仔细系好,衣服的下摆整理干净,然后慢悠悠走出门,身姿笔挺地站着等电梯,反而很可能只是一脚踩进鞋里去,耷拉着脚后板,冲进电梯以后,用手指抠着鞋子的脚后板,才勉强算是把鞋穿好,而且电梯的上下速度又没人能定得着,这个人可能还会在心里面不停的默念快下去了,怎么这么墨迹?甚至于联想能力大开,想一大堆有的没的的事情。”
“节奏不单单是个人的节奏,还包括剧情的节奏,但剧情的发展都是基于人的,如果他们剧情发展到一定的高潮部分,两人之间有一定的共鸣性或者情感的张力,那么这个地方的节奏一定会高涨,一定会快,但平时的情况下,如果你硬要把节奏拉快的话,反而会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对于节奏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方秉尘他们说的,平时可以多观察,观察生活里的节奏,观察人和人之间交谈的节奏,然后再把握到笔里面去。”
谭素恍然大悟:“诶,照这么一说,写的太平,归根结底可能是因为没有把冲突的点拉起来,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详略,所以导致整篇文章如流水,是吧?”
“可能如流水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甜梓眯了眯眼:“一个人有一篇文的习惯,而且慢慢来就好了,说不定今时不同彼时,来日不同往日。”
徐照月接下了甜梓的这句话:“是啊,而且我觉得你在写作之前,首先要先相信自己的笔,自己的能力,其次,要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或者说自己所建构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人物,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信任的话,那么人物就很难活起来了,首先是信任,其次写的时候,还是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看法,一个人有一个口味,如果是有意义的建议,你当然可以去听,你自己揣摩出其中的味儿来,也是你自己无形中的改进和完善,创作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创作本身很难脱离于人或者人群,又或者是某一种共同体式的命运,意志,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左右你,在你足够相信自我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妨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