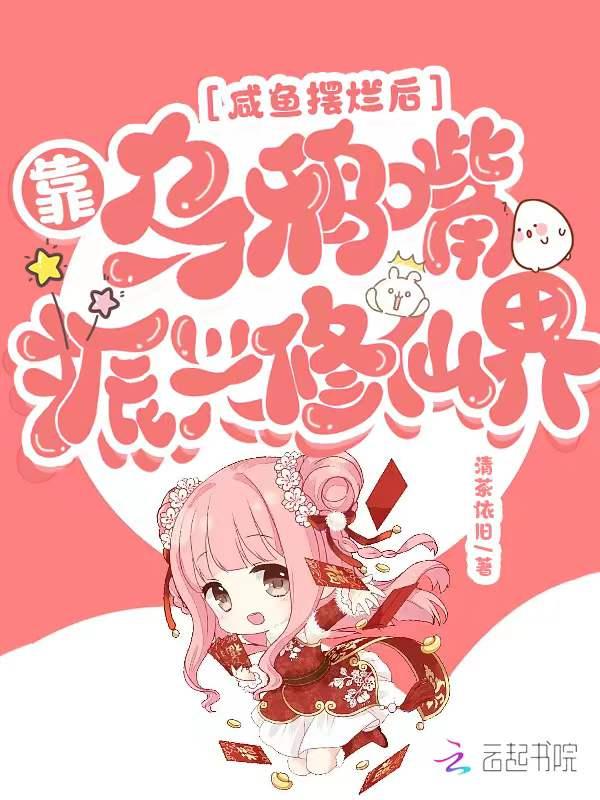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宠姬她一心要考公 > 冬夜春(第2页)
冬夜春(第2页)
既不想光明正大做他的妾,那便做一见不得人的外室罢!
“你做甚!屈邵!”
却没有得到回话。
苏远澄的挣扎不过如蚍蜉撼树,抵挡不住屈邵的强势。她绝望地阖眼,自知逃不过这一遭,而屈邵也绝不是李承恩那般好对付的角色。
但她还是不甘心抓住屈邵解她衣带的手,紧咬下唇:“等等,死也让我死个明白。你是何时得知我在卫邑的?又是如何得知的?”
虽时间紧迫,但她自认为计划周全。灌醉屈邵,利用他骗得通关文书,趁他熟睡,一路披星戴月跑马出梓州。
为迷惑可能的追查,她故布疑阵。用莺莺假扮自己争取了几个时辰,假托乐营姐妹办了去闽南的路引,甚至假意登上去往边关的船只。
况且她以盔甲覆身,以黄泥覆面,遮去了一切女性特征。
且为了加一重保险,出了梓州她便舍了文书,改用一早就离开了梓州的赵福娣的身份。
她实在想不明白,这其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屈邵见苏远澄神色清倔,却又不得不向他低头求解,只觉心头涌起一股奇异的畅快,宛若胜了一场不见血的仗。
他停下手,俯身靠近,温热的气息打在她的耳畔,湿润的唇舌让她震颤。
屈邵戏笑着,声音含糊道:“阿橙,你的耳垂……还是那么敏感。”
苏远澄登时反应过来,心神大震,难以置信地望进屈邵沾染欲色的笑眼:“那两次,你都没醉,是也不是?”
尝得了甜头,屈邵侧过身,支起手肘,托着下颌,指尖摆弄她鬓间的碎发,难得大发慈悲给她解释道:“我自小喝不醉酒,再烈的酒皆如饮水。”
他一直是清醒的。这个认知打懵了苏远澄。
那他怎么做得出向自己撒娇强吻,还要自己主动亲他之事?
回想起为了离开而付出的初吻和尊严,当时只当他酒醒后也不会记得,而如今……
苏远澄涨红了脸,咬牙追问道:“就算你去查了通关文书,找到我的行踪也需几日时间,那时我早已出了梓州,换了身份,你又是如何找到我的?”
难不成他真的手眼通天?
屈邵哪会告诉她,屈家暗探遍布边城,更何况屈家深耕兵伍多年,只要有驻军之处,不管城门守卫还是皇城禁卫,都有他的眼睛。
莫说查个通关之人,若有必要,陛下的踪迹他也查得。
他也不直接回答,只轻笑拨出她紧咬的下唇:“阿橙,你的计划不错,招招皆在拖延时间。也的确奏效了。可你犯了几个错误:轻信自己判断,这是其一;轻视对手实力,这是其二;轻易放松警惕,这是其三。”
苏远澄心中惊惧,原来她自以为的小聪明,在他面前仿若无所遁形。她张了张口想为自己辩驳,却不知辩些什么。
判断他醉酒断片,确实只凭直觉,认为他找自己行踪需要几日,确实只是预估,料想已改头换面给盼第去信,更是她自大之举。
见她鬓发纷散,樱唇微启,双眸失神,往日倔强狡黠的眉眼却因他笼上一丝迷惘与轻愁,屈邵不由呼吸一窒,喉结因吞咽而滚动,隐秘之处不可控地成形。
要怪就怪,她生得一张这般合他心意的皮囊吧。
屈邵俯下身,轻咬苏远澄精致的锁骨,声音因欲起而显得低沉沙哑:“阿橙,我可比书院那帮老腐朽厉害,你想学什么,日后我皆可亲自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