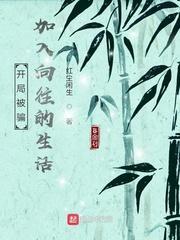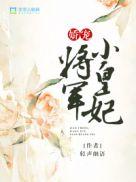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状元郎 > 第二百六十九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2页)
第二百六十九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2页)
他想起幼时父亲病逝,家中贫寒,母亲靠织布供他读书。冬夜无炭,母子二人围炉而坐,他诵《论语》,她纺纱线,纺车吱呀,伴着雪落屋檐的声音。他曾发誓,必要金榜题名,让她安享晚年。
如今第一步已成,可前方之路,更为艰险。
酒过三巡,宾客渐散。苏录独坐院中,仰望星空。北斗七星清晰可见,斗柄指向东方,正是春分时节。
这时,一道身影悄然走近。
“恭喜苏兄。”来者是此次同榜第七名的李慎之,籍贯江南,素有才名,平日寡言少语,却不料深夜来访。
“李兄何必多礼。”苏录起身相迎。
李慎之坐下,低声问道:“苏兄可知今科主考是谁?”
“听说是礼部尚书杨廷和大人。”
“正是。”李慎之点头,“此人掌文衡十余年,最重文章气骨。你那篇《君子不器》,破题奇崛,议论纵横,又不离圣贤本旨,必入其法眼。”
苏录一笑:“侥幸而已。”
“非也。”李慎之正色道,“我细读三遍,愈觉精妙。尤其是‘大用无方,大道无形’一句,既有阳明先生‘心即理’之意,又暗合伊川‘体用一源’之说,可谓融通古今。若非胸中有丘壑,断不能为此文。”
苏录默然。这些思想确是他近年来潜心钻研所得,尤以王阳明心学为根基,辅以程朱理学之严谨。但他不敢明言推崇阳明,毕竟其学尚遭朝中保守派攻讦,若在考场上露出口风,反招祸患。
“李兄厚爱,愧不敢当。”
李慎之忽而压低声音:“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讲。”
“你此文一出,必有人妒。第五名看似风光,实则已树敌无数。尤其那些屡试不第的老翰林,最恨后生夺魁。你若想更进一步,须得小心行事。”
苏录心头一凛。
他从未想过自己一篇文章竟能引来风波。但转念一想,科举本就是名利场,有人欢喜,自然有人嫉恨。
“多谢提醒。”
李慎之起身告辞,临行前留下一句话:“三年后会试,若你还记得今日之言,或可全身而进。”
夜风拂面,苏录久久伫立。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寒门学子,而是踏入了权力与舆论交织的漩涡中心。
数日后,捷报传回家乡。村中敲锣打鼓,族长率子弟焚香祭祖。苏母含泪焚纸钱,口中喃喃:“夫君在天有灵,儿已不负所望……”
与此同时,京中亦起波澜。
内阁值房内,杨廷和手持苏录试卷,反复品读。良久,对身旁侍读道:“此子文中有浩然之气,非死记硬背者所能为。且见解通达,不拘泥于章句,颇有古之遗风。”
侍读笑道:“大人既如此赏识,何不记下姓名,待会试时留意擢拔?”
杨廷和摇头:“不可。吾为主考,当持公允。若早早留意某人,反害其成长。况且……”他顿了顿,“真正的人才,不需要提携也能冒头。”
话虽如此,他仍将苏录试卷收入私匣,并批八字朱批:**“根器深厚,前途未可限量。”**
此事后来辗转流传至国子监,乃至六部衙门。有好事者开始打听这位“第五名经魁”究竟是何来历。
有人查到他是南直隶凤阳府人,三代务农,父早亡,母纺织度日。如此出身,竟能脱颖而出,顿时引发热议。
清流赞其“寒门崛起,士林之幸”;权贵则冷笑:“区区乡野匹夫,也配谈经论道?莫非朝廷取士,今后要看谁更穷不成?”
更有甚者,在诗社集会上作打油诗讥讽:“五更灯火十年苦,换来一张榜上名。莫道书生无胆气,见了官老爷腿先软。”
风言风语,不绝于耳。
苏录皆充耳不闻。他租下一间小院,闭门读书,每日清晨诵经,午后习策论,晚间则研习历朝典章制度。他还特意抄录《大明会典》中有关赋税、屯田、漕运诸章,逐条分析利弊,写下万言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