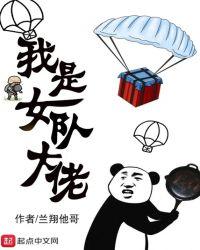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于她掌上 > 谕旨赐婚(第2页)
谕旨赐婚(第2页)
“她这么个混账东西,不侍婆母、谮毁小姑,将孩子们教养的各个无理、不分尊卑,可谓是贱人暴贵!”
成燮奉来清茶让皇帝漱口。
接着杯盏,成燮低头垂目,十分恭顺地开口说:“娘娘凤体贵重,何必为这等卑劣妇人伤及身体。听说,那小女子性情刚烈异常,弄得一身血肉模糊,仍然奋力求生!”
皇后宣其霭气地只骂荒唐,皇帝面色好些后,她便恭敬地说:“京中风气坏到极点了!纵然是清河那般只知玩乐的孩子,尚且没有苛待没有血缘的继子女们,何况他阎鸻敬人还没死呢!娘亲舅大,他这个舅舅不如割了头颅死了好!”
皇帝皱着眉打断她,道:“皇后!朕知道你痛惜孩子,但是阎鸻敬罪不至死,你不要借题发挥!到底是有功之臣,阎鸻敬顶对是疏忽,好歹那孩子没有生命危险,朕罚过他就算了!”
成燮不愿帝后不愉,便抢着说:“毕竟世子还在南省,娘娘还得顾虑陛下的为难。”
宣其霭扭过头去,仍是气愤难平,道:“陛下不是母亲,自是难以体会臣妾的痛心之处!当年最是畏难时,韩吴二妃多么罪恶奸诈的妇人!她们围了府邸想要逼陛下就范,臣妾身怀有孕不能抵挡……若非阳宪公主施以援手,臣妾这条命……”
“……好了,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知道姑母对连氏不满,但当年朕是真的看走了眼,不知道连太妃那般好的人,她的子侄中竟有连氏这般跋扈之人!”
“皇后!你也不要过于爱屋及乌了。”
得到了皇帝的妥协,宣其霭很有分寸,她恭谨地点了头,皇帝便起驾御书房。
梦珂叹口气,卷起了珠帘,劝道:“娘娘啊,何必对阎家发这么大的火?嘉远公到底是中流砥柱,日后大皇子继承大统,怎能没有他的鞍前马后呢?”
宣其霭抚着自己的散发,平复了脑后的盘发,她依靠着床头说道:“阎家就是太滑头了!皇子们长成他却带着头不愿意站队,那就没有拉拢的必要。”
“像这样的世家,站了队就是冒了大风险,不愿意自然,我们拉拢不到,更何况是别人呢?只恨陛下年岁上涨,不似从前般锋利……”
“本宫能压下一个楼家,自信没了阳宪公主掌舵的阎家也不是问题!”
梦珂不解,小心说:“楼家站队三皇子自然该打压,可毕竟是阳宪公主的血脉,娘娘尚且顾念孤女,何必摧折之?”
她平直的唇,唇角有了些笑纹。
她起身走到明镜前,看着自己日渐浮起的颈上细纹,说道:“公主在意这一支血脉吗?阎崇皑匹夫罢了,若非国朝陷落,你真当先帝爷看得上这卑劣的血脉?公主看中的只有一支血脉,那就是阎雁栖的孩子。”
“我帮那个孩子才是真的报答公主啊。”
梦珂疑惑,转头点了安神香来放到近处。
“世间真有公主这般所思所想的人吗?”
宣其霭垂眸,探出素手拨弄着玉枕。
“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早朝罢过,皇帝没什么心情批阅奏折,他遣人把阎鸻敬从府中提溜出来,憋着怒火欲狠狠责骂一番。
可平心而论,即使纲常受损,但云泥之别岂能同日而语?
他叹口气,拿起阎湜彧的密奏一气看了下来。
文本特意写的如此臭长,简略概括,有用的不过是几句:关系重大,牵扯京僚,彻查与否全赖陛下旨意,臣欲先行回家。
气得皇帝胡子捋地颩颩的,他收起文本,一股脑塞进了条盒里。
成燮却在此时前来复命,他道:“陛下,外头递了牌子,翰林院编修、新科进士探花郎褚靖徽特此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