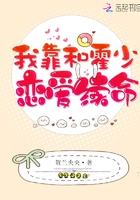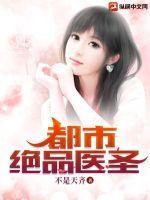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钻狗洞后爱上小奶狗 > 13民族图谱九(第2页)
13民族图谱九(第2页)
只看了几秒,他便道:“数据库里也不可能囊括所有配比,尤其几百年前,很多矿物颜料都是师徒私传,因地制宜,而且又是手工冶炼,掺配比例也因人而异。”
他说话的语速不快,却异常清晰,像是将林序南那盘根错节的思绪一寸寸理顺。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还原描金线的颜色了。”林序南低声说,声音有些发哑,“我查过文献,关于类似这种描金线的配比,也比对过了,误差依旧很大。”
他的嗓音压得很低,像是不愿被察觉自己的不确定。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林序南顿了顿,又抬起头看向裴青寂,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自觉的期待。
这一句“你”,说得很轻,却藏着一种只有在极疲惫时才会显现出的信任。
他忽然想起裴青寂曾凭记忆绘出残破图谱的完整纹样,也许……眼前这个人真的还有办法。
——哪怕只是个猜想,他也愿意相信。
他不知道,这种被看见、被依赖的感觉,也让裴青寂的眸光沉了几分。
裴青寂想了想,转身从角落的矮柜里抽出一叠宣纸,顺手拿过一支簇新的狼毫笔,在操作台边站定,执笔蘸墨,在纸上一边思考,一边端端正正地写下:朱砂,石绿,赭石,云母。
墨迹迅速浸润开纸面,他的笔锋却不带一丝犹豫,他在下方依次列出这几种矿物颜料中常见的金属成分——汞,铜,铁,铝,镁,钾。
他将纸张稍稍转了一个角度,手腕一偏,便开始勾勒线条,将矿物与金属成分依照可能的生成路径一一对应。
那是一种极有逻辑的结构图,几乎可以称为“关系解剖图”。
林序南站在他身后,看着那幅纵横交错的“矿物-金属”图一点点铺开,每一道线条,既像手术图解,又像剖析一部失落配方的脉络。
裴青寂下笔很快,却没有一丝凌乱,他的笔锋收放有度,线条分明,每一笔都像是在纸上描刻历史的骨架。
有温度,也有分量。
“金光,不单单是‘金’色。”裴青寂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林解释,“有时,是多金属反射下的‘伪金’冷辉。用银掺镁,再微量加铝,能压低整体色温,反而更接近古籍中那种清亮又内敛的光泽,更像真正的冷金光。”
林序南听着,眼神微微动了动。
裴青寂忽地抬眼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轻,却像一块安静落地的石头,击中水面,泛出一圈极浅的涟漪——没有过多语言,却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安慰与肯定。
就好像是在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剩下的,我们一起来。”
他又在下方继续写道:
铜:4–11%
铁:2–7%
铝:5–9%
镁:1。2–2%
钾:波动大,需实验排除干扰项
他根据传统颜料制备工艺中金属氧化物的共熔温度与颜色呈现关系,将各个成分按理论区间进行组合,筛去可能导致颜料毒性增强或易氧化变色的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