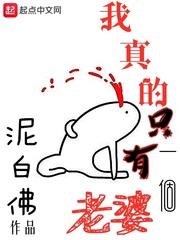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丫鬟打工日常 > 第 82 章(第2页)
第 82 章(第2页)
而谢渊只当看不见那几人看好戏的神情,也无视了谢集英话里的小心思,他抬手见礼,声音不卑不亢道:“谢渊见过几位前辈,今日有幸同来赴宴,诸位风采出众,气度不凡,定然皆是才思敏捷之人,谢渊不敢妄称胜蓝。”
他余光扫到巧思雅致的园景,又接着道:“今日得见县尊园中曲水流觞之景,倒让晚辈想起《兰亭集序》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不知诸位方才可曾品鉴过枕流园的龙湫?看起来引的应该是活水。”
几人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露出几分迷茫来。
其中一人下意识喃喃道:“龙。。。。。。?哦!你说后头那池子,贤侄真是好眼力,不过这龙湫比起南边云栖园的还是小了些,去年我去。。。。。。”
他话未说完被旁边另一人打断:“得了吧,你上次连《水经注》都能念岔字,还学人品鉴呢。”
几人这回都是托了家里子侄的福,时隔几年又接到了县令的请帖邀他们赴宴,进了园子还没来得及好好观赏,便凑到谢集英这头来了。
本还想趁机打趣几句,谁知却被谢渊几句话就堵了回去。
这几人读书才学不见得多出众,日常派头倒是摆得不输阵,只可惜对外人摆谱他们虽团结,但若有一方想要冒头必会被对方拆台。
眼瞧着他们一言不合就要争辩起来,此时却忽然走过来一位青袍管事,只见他对谢渊含笑道:“公子竟识得这龙湫?此乃我们老爷特意命人仿大龙湫瀑布所建。”
他看向谢集英颔首行礼道:“谢举人,不妨带上谢公子,随我去观瀑亭细赏?”
谢集英已认出这是县令身边的长随,他的视线落到远处的观瀑亭,有一紫袍男子正在亭中负手而立,身边还守着两个伺候的丫鬟,他神色一凛,对那长随正色道:“有劳了。”
说罢谢集英几人抬脚离开,没被邀请的余下几人也看到了观瀑亭里的身影,心中忐忑地面面相觑,倒是此时都回过神来,他们跟谢集英早已不是同一路人了。
崔卯年过五十,却依旧腰背挺直如松。
他侧身站在观瀑亭的雕花栏杆前,紫袍下摆被风微微掀起,露出一双云纹官靴。
保养得宜的面庞上几乎不见皱纹,唯有眼角几道细纹在阳光下若隐若现,倒像是刻意留着彰显威仪的痕迹。
谢渊终于见到这位太康县令,与他想象中的不同,崔卯面上看起来很是和善。
那双背负着的双手白皙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右手拇指上戴着的翡翠扳指泛着幽光。
这全然不像个地方官员的手,倒像是翰林里那些终日执笔的清贵文人。
这在谢渊眼中,越发觉得此人带着股道貌岸然的意味。
“集英见过大人。”谢集英躬身行礼,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
谢渊也顺势道:“谢渊见过县令大人。”
崔卯转过身来,脸上果然带着温和的笑意,眼角的细纹随之舒展。他抬手虚扶:“今日私宴,不必讲究这些虚礼。”声音清朗,丝毫不见老态。
他视线又落到一旁的谢渊身上,见眼前少年身姿挺拔如青竹破土,眉目清朗疏阔,目光沉静从容,还带着股超乎年龄的持重,在这园子的一群人中显得格外出众,不由感叹这谢集英倒是生了个好儿子。
“你就是谢渊?方才你好像对我这园子的龙湫有几分见解,可是去过南方?”
谢渊微微躬身,语气从容:“回大人,晚生惭愧,未曾亲至南方。只是平日听先生讲解《水经注》《舆地纪胜》等书,见其中记载雁荡山大龙湫飞瀑悬空,如白练垂天,适才见园中引水叠石之妙,颇有几分神韵,故而斗胆猜测。”
崔卯点头,让人在一旁石凳落座,又让丫鬟上茶。
“你在城外的书院上学?听说那位陈山长收学生极严,怎么平日不忙着钻研四书五经,倒有闲暇涉猎《水经注》?”
听他提起书院,谢渊开始猜测他的目的,面上却恭敬垂眸回道:“先生确实从不在课业上允许我等马虎,只是他道经书是米粮,杂学是盐醋,若只囫囵吞米,终究食之无味,所以平日常让我们多看这些典籍来佐证经义。譬如读《禹贡》时,便叫我们对照《水经注》看九州山川脉络。学《春秋》时,又让参详《左传》《国语》互证。晚生愚见,山长是要我们明白圣贤之道本就在天地万物之间,非独在书本上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