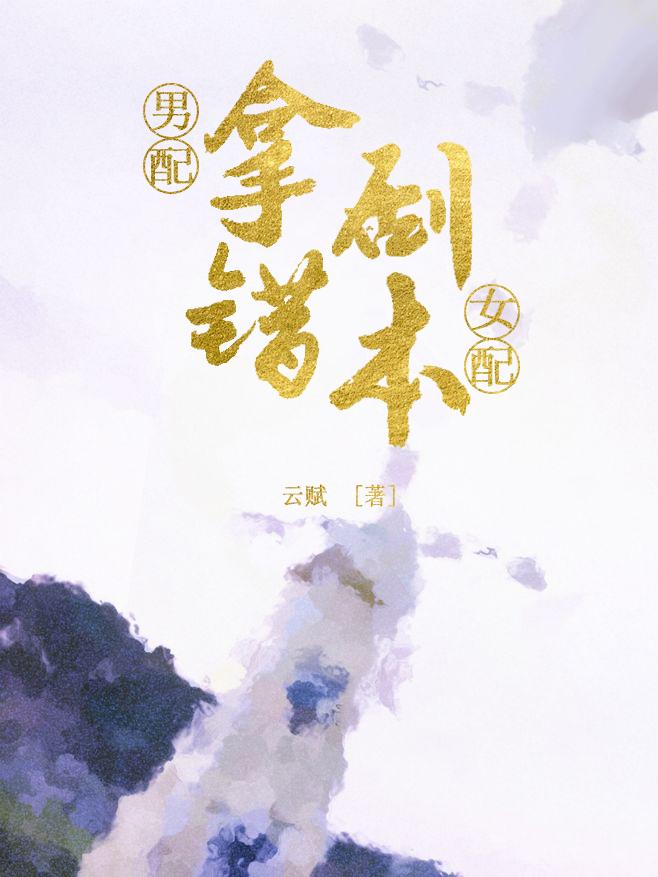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作精少爷饲养手册 > 8090(第12页)
8090(第12页)
冬青谨慎地回答道,他问一句就答一句,绝不往下多说。
“哦,没有其他的了?”李兰钧问,眼神不住往包袱里的小袋上望。
“有……”冬青生无可恋地拎起那袋银钱,埋着头道,“叶姑娘、还给您送了银两来。”
李兰钧一顿,蹙眉道:“什么意思?”
“一共是五十五两,碎银加上小铤,一分都没少。”冬青闭上眼,豁出去解释道,“少爷,南园赎身的价钱,是五十两,叶姑娘还多给了些……”
李兰钧眼前一黑,他撑住扶手稳了身形,勉强没呵斥出声,颤声问:“她有说什么吗?”
“那日没来得及还清,今日还来,日后两清了。”冬青一字不差地复述门房传来的话。
“两清……?”
李兰钧手里的磨喝乐都成了诀别之物,他盯着那只憨态可掬的玩偶,想从中找寻另一种可能,“怎么就两清了!我没答应过,她就敢说两清?她在哪儿?我要见她,我要她当面同我说,我不信这是她的话!”
他站起来,忍住满目眩晕,一步步要往寝居外奔走,却因病弱只能缓步徐行。
“少爷,她已经走了,送了东西就走了。”冬青忙扶住他,苦口婆心地劝道,“老爷他们就在前厅,等着您去庆生呢,咱们不妨先过了生辰,日后再去同她说清也不迟?”
“迟了!她就要跟人走了!她就要丢下我同别人在一块了!”李兰钧魔怔地朝他吼道,身子随着高喝更是摇摇欲坠。
“少爷,是您亲口放她走的,既然她已经与南园无关了,您又何苦再去寻不痛快呢!”
冬青搀扶住他的胳膊,见他又要发作伤身,几乎声泪俱下地劝说道。
我后悔了。
李兰钧脑中很快蹦出这四个字。
他一阵惊诧,手忙脚乱地向四周看去,像是怕有人听到他的心声似的。
“对,你说得对……”他连连点头,只是一个劲地肯定冬青的话,“对、对,我和她再也没有关系了。”
“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说着,猛地看向手中制作粗糙的玩偶,看着玩偶线缝的眼睛道,“你施舍我,你以为我很可怜吗?我不需要你可怜!”
玩偶无辜地睁着黑溜溜的眼睛。
李兰钧扬手,用力把磨喝乐扔在墙角,让那光鲜的女娃娃陷在杂草泥土当中。
他拂袖,撑着院墙走出别院。
两月的光景,南园天翻地覆。
李兰钧遣散了半数家仆,整日坐在院子里侍弄花草,他一反常态地放缓了急躁脾气,写写画画,围着花园中那些鸟雀珍禽打转。
可惜好景不长,告假的请奏到了末尾阶段,知府大人派遣一众衙役,架着他上了佥厅办事。
前通判兼任代通判杨遂终于功成身退,将案上小山高的文书扔到他面前,拍拍屁股坐在佥厅侧座等候下值。
李兰钧斜倚在高凳上,面色不善地看向他。
“翰林大人怎的还不走?”
杨遂一挑眉,揶揄道:“哟,李大人,您的心病这就好了?能跑能跳的,还能出声呛人了。”
“李某哪来心病可言,不过是例行病程,年年都要在鬼门关里走一遭才行。”
李兰钧冷笑一声道。
“哦——”杨遂故意把这声拖得老长,“杨某心思古怪,以为李大人故作洒脱呢。”
李兰钧嘴角一抽,无力反驳,只得干巴巴地说道:“哪里……”
杨遂眯起眼睛,用敷衍的笑脸回答他的掩饰。
李兰钧装模作样两月的温和谦卑差点破功,他收回目光,把视线投向桌案上的公文中。
不知是否病入慧门,脑子生了锈迹,处理半晌才几本公文,远远不及往日的迅疾。
“夫人!”
杨遂那厮忽然高呼道,随即化作一阵黑风从他身旁蹿了出去。
佥厅门口立着一名女子,提着食盒犹豫再三不敢踏进,听到他的呼唤,抬头从满面羞红里脱出几分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