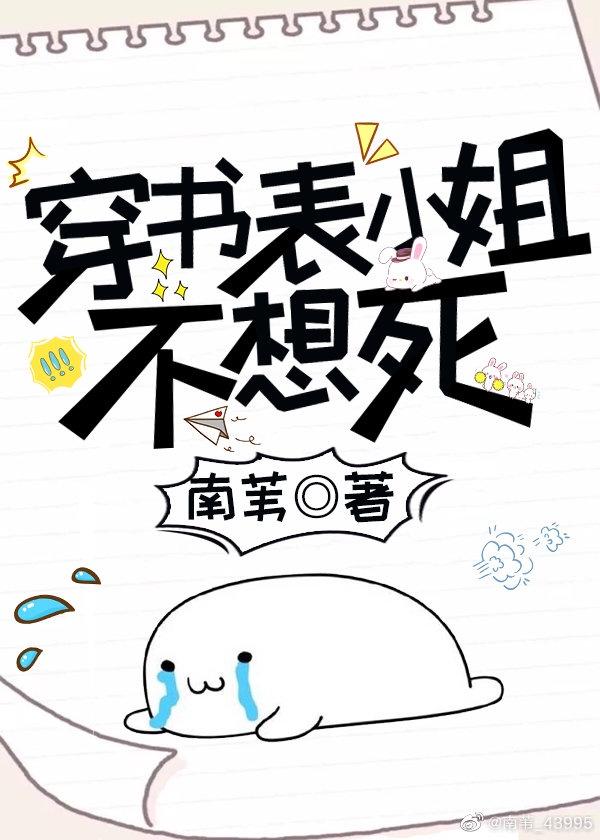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祭司她盯上我了 > 6070(第4页)
6070(第4页)
“可惜看来即使是她也失败了。”墨拂歌垂眸,难得流露出悲悯神色。
死而复生之事,谈何容易。若人死皆可复生,那世间又何来如此多生离死别。
“自然,即使是创造生命,创造灵魂的容器,也要比召回离散的魂魄归于本体简单。”苏暮卿指尖轻轻拂过冰床红绫,“苏渺然也是根据苏辞楹遗留手札上的研究,创造出了我。即使已经做到如此地步,即使是苏辞楹,也无法唤醒闻弦的魂魄。”
墨拂歌深深回望一眼冰床上相拥二人,“墨怀徵当年手札记载,玄靳在墨临城所布下的篡夺龙脉的阵法,不知是从何处请来的高人,她看不出门道,只能请来已经退隐回清河的苏辞楹来研究阵法。苏辞楹与墨怀徵曾是生死托付的至交,研究后尽力帮她毁坏了部分阵眼。所以无论后世如何传闻她余生疯癫,我都不相信能做出如此精密之事的,会是疯子。”
“只是如今看来,她不是疯子,只是”一声轻叹,“只是痴人罢了。”
至情至痴,才会妄图逆天改命,逆转阴阳。
墨拂歌随着苏暮卿走向冰室的里间,里间中存放着各色书籍与手札,看上去都是苏辞楹亲笔所留。
或许是因为处于特制冰室的原因,冰室中的物品都保存得格外完好。她打量里间,意外发现了其中珍重摆放的一把古琴。
上前一看,是一把桐木冰蝉丝的七弦琴,出于对琴艺的喜爱,她下意识地抚摸上琴弦。这把琴做工精致,用料名贵,木料上烫金纹漆,雕刻成凤求凰的形状,一看便是万金难求的稀世名琴。
可惜她刚想弹奏,便感受到因为多年在极寒中封存,琴弦已然生涩,并不适合弹奏。
她也知晓,这是苏辞楹的爱琴,能够带入冰室同葬必然有其意义。最终也只是爱怜地抚摸过琴弦,将桐木琴重新摆放好。
就在此刻,苏暮卿拿出一卷书札递给了墨拂歌,“这应当就是苏辞楹当初留下的记录,记下了当年对墨临城中阵法的一些推算。”
墨拂歌接过书卷,匆匆翻看着书札中仔细记录的繁复字句,这些记录词汇生涩,要带回去再做仔细研究。
她信手翻阅到书札的最后一页。
书页上的字迹清隽,笔锋亦是缠绵缱绻。
“弦上相思已覆雪,花前别泪难为辞。”
明明是缠绵的字迹,却是字字泣血。
“丁未年十一月廿九。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何处寄书得?”
“戊申年四月十一。已数不清这是你多少次入梦,经年相思,也只在梦中片刻温存。”
“庚戌年十一月十三,大雪。雪落三日,天地皆白。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辛亥年三月初七。往苗疆去,花开正好,恰如当年,手植清昙一株于女娲大神下。犹记昔年你于此立誓,说永结同心,生当同衾,死亦同穴。”
“欲寄梅花,莫寄梅花。”
——
附《梦呓集闻弦》
漫天流萤飞舞,荼蘼花开至绚烂,白色的花瓣扑簌摇落。夜风吹动她白衣墨发,耳畔依旧回荡着先前的悠扬琴声,萤火闪烁间那张熟悉面庞的温柔神情像是最深的湖泊,一旦落入那双桃花眸里,就只能心甘情愿地沉沦其中。她的目光一寸不移地系在我身上,我却能看见她抱琴的手因紧张而用力,手指蜷曲出漂亮的弧线。萤火落在她一双浅紫桃花眸中,潋滟开一片浮动星光。
‘阿弦,手给我。’她轻声道。
我将手递给她,她指尖点在我掌心,勾画着古老的符文,冰凉的指尖在掌心摩挲,微微的痒。而流光从她的指尖四散开来,枝蔓在我手中缓缓生出,蜷曲伸展,最后开出一朵素白昙花。
【作者有话说】
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何处寄书得?——晏几道《思远人》
哈哈,全是女同。
对不起,真的很喜欢苏辞楹。喜欢到想为她单独写一本书。
63回京
◎她已经演了十年,不缺这一时半会儿。◎
自北往南班师回到墨临,气温也渐渐回暖,南归水乡,听棹歌声声,莲子红透,盛放于碧波清塘。
叶晨晚忽然意识到,比起北地的寒凉,她或许已经习惯了江南水乡的温暖。
她此次班师回朝,也是引得多方势力关注,毕竟在洛祁殊与燕矜二者互相掣肘的关系中,终于出现了制衡的第三者。
面见玄若清时,座上帝王面色深沉,不痛不痒地夸赞了她几句。二人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宁山那座金矿,玄若清只挥手,就赏赐了一堆贵重之物,君臣无话,叶晨晚安静地领赏退下。
或许在外人看来,叶晨晚于此事上着实冤种,魏人入侵这个烫手山芋被推三阻四无人愿意接下时,只有她出面担下了这件麻烦事。辛苦出征为皇家解决了这个麻烦后,也只不过得了不痛不痒的金银赏赐,却无实权分封。到头来,她还要继续做这已经做了十年的质子。
但叶晨晚知道玄若清想要什么,北地的宁王府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名将,宁王府不需要耀眼,只需要安分守己,能护好北方广袤的边境免于魏人侵袭便可。
玄若清需要这么个懂事安分的庸才,那她也乐得暂时扮演,她已经演了十年,不缺这一时半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