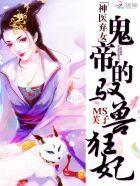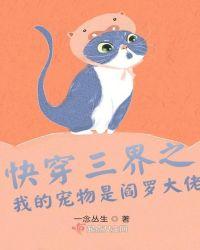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广夏:文德皇后 > 亲迎(第1页)
亲迎(第1页)
冬日的黄昏总是来得分外早,所以李家迎亲的队伍未时就出发了。
阳光并不耀目,却有些异乎寻常的活泼跳脱,一片片碎金好似潜翔许久终于跃出水面的游鱼,在李家迎亲的队伍中欢快地腾挪闪转。
清透的空气顿时荡漾出金色的涟漪,与銮铃、琵琶、箜篌共振。跌宕起伏的音符就这样荡漾在迎亲队伍中每一个人的心头。
作为媒人窦抗的侄女婿、新郎亲点迎亲人、李渊夫妇公认的李氏同辈宗亲最牢靠的兄长,李孝恭却从来没有这样烦躁过。
“你可以把怀里那对大雁给我。本来就捆紧了,准保逃不走。你现在一手挽辔,一手攥紧了大雁,快把大雁掐死了。这一对大雁怕是撑不到放生就要被捂昏过去了!”他试图耐心劝说与吉服、大雁和紧张抗争的从堂兄弟。
“这身爵弁服不舒服。刘娘子一定误把去年的尺寸交给了缝作匠……”新郎李世民抱怨着挪了挪身体,连坐骑也烦躁地嘶鸣来几声。
“头上也沉。”李世民一边抱怨一边询问,“兄长,我的簪导歪了吗?”
李孝恭感觉自己一辈子的耐性一半用在自己婚礼上,一半怕是用在堂弟的婚礼上:“没有歪。大喜日子不准胡说八道,礼服很合身,只是宽袍大袖你穿得少而已,到了高府多走几步路你就习惯了。不要疑神疑鬼!”
“兄长,催妆诗的第一句是什么?昨晚我明明背熟的,现在又忘记了。”李孝恭还没来得及回答,骑马抢在队伍最前端的李道玄打了个恶作剧的呼哨,做了个鬼脸。
“有人还没见到新妇,就慌成这样子了;一会儿见着了,还不知吓成什么模样!”十一二岁的小郎君惊诧于自己一向崇拜的兄长此时竟有如许多的局促难看之处,顿感滑稽万分,发出不可置信的诘问。
“我没慌,你再胡说小心我揍你!”李世民从腰间抽出竹笏板吓唬李道玄。
他的反驳过于激动,导致怀中的大雁在彩色丝带的束缚之下仍然奋力挣扎。他只得放弃虚张声势地威胁幼弟,紧紧护住大雁。
“都不准吵!今日出门迎亲这些大小郎君,真是一个都靠不住——还有你长兄也靠不住!建成没有告诉你把催妆诗和却扇诗写在笏板上吗?”李孝恭扶着额头。
“没有,他昨天刚到大兴,一时兴起喝得烂醉。我和他都没有说上几句话。我阿娘说,孝恭兄长办事比毗沙门稳重,道宗和道玄模样比三胡周正。所以他们回不回来,于我们迎亲也无大碍。”这番坦率的说辞倒是让李孝恭舒怀大笑。
“谢叔母抬爱了。我差点忘了临行前她给我这个——接着!”他说罢将一个嵌有珊瑚珠的同心环扔给李世民,“宝石后的暗格里藏着绢布字条,到时照着念。”
在李世民接过同心环,打开暗格,记诵催妆诗的当口,李道玄匆匆下马,贴近白蹄乌,劈手夺雁,一气呵成。
被捆紧了喙、翅、腿的大雁扭了扭唯一自由的脖颈,庆幸自己居然还活着,就松松爽爽躺在小郎君的怀中,等待着被抛掷又被放生的曲折命运。
李世民这次似乎也没了火气,也没有再拿笏板吓唬这位自己亲自选中同去迎亲的堂弟,只是千叮万嘱:“道玄,你替我看管好大雁,不要有什么闪失。”
李道玄不悦地撇撇嘴,觉得自己心中无所不能的从堂兄今日变得分外婆妈与不可理喻,一路絮叨个没完,一点也不像往日那个运筹帷幄、胜券在握的兄长。他不禁有些失望和恍惚,被翻来覆去的询问烦到头痛时,李道玄甚至想一走了之——他只听父母说婚礼时愉快的、热闹的,并没有人告诉他新郎是拘谨的、不安的并把他也感染得忧心忡忡。
“结婚真是太可怕啦!可是我又不能弃兄长而去!”这个天真聪明的小顽童自宽自解,“一会儿到了高家,新妇的同族兄弟们一定准备好了竹杖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兄长穿着这一身大袖爵弁,手中只剩竹笏。被人一拥而上围攻也不占上风,正是我大展拳脚的好时机!到时定不能让新娘家人看清了我们李家儿郎。”
想到名正言顺地为家族荣誉打架,十一岁的孩子莫名兴奋起来,挠了挠大雁的脖子,顺势将它装进镂空的箱箧中,置于鞍上,心情一下子从谷底迅速爬升到山巅。
李孝恭继续被连弩般无聊的问题扎得脑子嗡嗡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