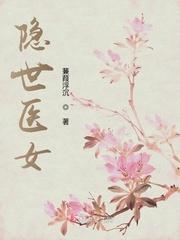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宋文豪 > 第241章 你们现在就是监生了(第2页)
第241章 你们现在就是监生了(第2页)
陆北顾闻讯,心中震动。他知,若欲为政,必先识世情,若仅纸上谈兵,终难成事。他思忖良久,决意应征。
当夜,他与周怀安、植仪海共聚亭中,将此意告知二人。
“陆兄真欲前往?”周怀安神色凝重。
“正是。”陆北顾目光坚定,“我既欲为政,便当知民生之苦,识军政之难。若只坐而论道,不亲历其事,终难成器。”
植仪海沉吟片刻,道:“陆兄所言有理。然边地战事,凶险万分,若无充分准备,恐难胜任。”
陆北顾点头:“我亦知此事非同小可。然若能以此磨砺己身,即便凶险,亦在所不辞。”
周怀安叹道:“陆兄志坚,令人敬佩。若需相助,我愿随行。”
陆北顾大喜:“若得兄同行,实为大幸。”
植仪海亦道:“我亦愿同行,共赴边地。”
三人相视一笑,心中皆生豪情。
翌日,陆北顾三人便向国子监请辞,报名应征。消息传出,监中震动,众人皆为三人勇气所折服。
临行前夜,陆北顾独坐书斋,望着案上《濂溪集》,心中默念:“心静,则理明;理明,则行正;行正,则德立;德立,则政行。愿以此心,行此道,不负此生。”
他缓缓起身,披上外袍,走出书斋,夜风拂面,星光点点。他仰望夜空,心中一片清明。
他知,真正的学问之道,才刚刚开始。
陆北顾三人应征边地军务之事,很快便传至朝中。国子监主簿亲自召见三人,询问其意。陆北顾神情肃然,拱手道:“学生虽未历实务,然志在为政,若不知世情,不识军务,终难成事。今边疆告急,朝廷需人,学生愿效微力,以试所学。”
主簿沉吟片刻,点头道:“陆生之志,可嘉。然边地战事,非同小可,若无准备,恐难胜任。”
陆北顾道:“学生愿随军幕,不求立功,但求历练。若能得一隅之地,亲历其事,必能有所体悟。”
主簿望向周怀安与植仪海,二人亦皆神色坚定,齐声道:“愿随陆兄同行。”
主簿沉吟良久,终是点头:“既如此,我便为你们引荐一人。”
三人闻言,皆露喜色。
主簿道:“此人乃兵部侍郎赵景明,曾久居边地,通晓军务。若得其引荐,可入边地军幕,虽无实职,然可随军观政,亦可得历练。”
陆北顾三人连忙躬身行礼:“谢主簿大人。”
主簿摆手道:“不必谢我,若真有志于实务,便当以心力行之,而非空谈义理。”
翌日,三人便随主簿前往兵部,拜见赵景明。
赵景明年约五旬,身形瘦削,目光如炬。他听主簿介绍三人来历,略一沉吟,道:“诸位皆为国子监生,才学自不必说。然边地军务,非同小可,若无实战之历,恐难胜任。”
陆北顾上前一步,拱手道:“学生虽未历实务,然愿以所学,辅佐军务。若能得一隅之地,亲身经历,必能有所体悟。”
赵景明目光微动,道:“你既愿历练,那便随军幕前往延州,协助军务文书,若能胜任,再议其他。”
陆北顾三人齐声道:“谨遵大人之命。”
赵景明点头:“好,三日后启程,不可延误。”
三人皆郑重应命。
临行前夜,陆北顾独坐书斋,望着案上《濂溪集》,心中默念:“学问之道,贵在实践。若不能以理应事,以德修身,以行证道,则所学终为空谈。”
他缓缓起身,披上外袍,走出书斋。夜风拂面,星光点点,院中银杏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似在低语。
他仰望夜空,心中一片清明。
翌日清晨,三人便收拾行囊,准备启程。植仪海与周怀安皆神色坚定,毫无惧意。
临行前,宋堂颐亲自前来送行。他望着三人,目光深沉,缓缓道:“诸君此行,非为功名,亦非为利禄,而是为求真知。若能以理应事,以德修身,以行证道,他日归来,必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