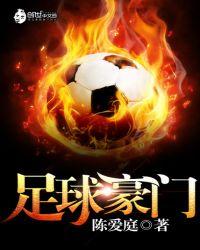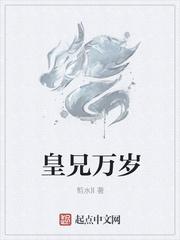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宋文豪 > 第241章 你们现在就是监生了(第1页)
第241章 你们现在就是监生了(第1页)
“何止意气!”杨安国甩袖道,“他竟与本官立下赌约,言道三日之后,就在这国子监内,派人与我国子监监生比试一场!考校真才实学!”
杨安国说到此处,脸上又气又急:“本官岂能怯战?当场便应下了!可回来细。。。
陆北顾步出明辨堂,迎着晨光,心中一片澄澈。他缓步穿过庭院,脚步轻稳,目光坚定。国子监内,书声琅琅,监生们或立于廊下诵读,或三五成群低声议论,一派求学之风。他望着这一切,心中忽生感慨:昔日只知埋头苦读,为功名所驱,如今方知学问之道,不在策论之巧,而在心性之修。
他正欲回住所,忽见前方一人迎面而来,身着青衫,步伐稳健,正是植仪海。
“陆兄今日听讲,可有新得?”植仪海笑问。
陆北顾拱手一礼,道:“今日所听,乃《孟子?尽心》篇,先生所讲‘尽心知性’之理,令我豁然开朗。原来学问之道,不独在于识字作文,更在于修心养性,通达天理。”
植仪海点头:“你果然悟得其理。然‘尽心’二字,非止于听讲,更须于日常行事中体察。若仅空谈义理,而不实践于身,终究是纸上谈兵。”
陆北顾肃然道:“兄所言极是。我已下定决心,自今日起,每日静坐一刻,格物一理,修身一行,务使所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植仪海微笑道:“如此甚好。然你可知,学问之道,亦如行路,需有同道之人,相互砥砺,方能不偏不倚。”
陆北顾略一沉思,道:“兄之意,可是要我广交同道?”
植仪海点头:“正是。你虽才思敏捷,然学问之道,非一人独行可成。国子监中,亦有诸多有志之士,皆可为友。若能与之切磋琢磨,互为砥砺,则学问自可日进。”
陆北顾闻言,心中一动。他平日虽与人交往,但多因科举之故,或论策论,或议文章,少有深入交心之人。如今回想,确觉孤行寡助,难成大器。
“兄所言极是。”陆北顾郑重道,“我愿自此广交同道,共研学问。”
植仪海满意地点点头,道:“你既有此心,我便为你引荐一人。”
“何人?”陆北顾好奇。
“此人名唤周怀安,乃江南士子,出身书香世家,素有才名,尤擅经义之学。其人虽年少,却沉稳有度,心志坚定,与你性情相近,若能相交,必有益于你。”
陆北顾闻言,心中欢喜:“兄既如此推崇,我愿一见。”
植仪海笑道:“他今日亦在堂中听讲,待会便可引你相识。”
两人边走边谈,不觉已至一处小亭。亭中已有一人端坐,身着青衫,面容清俊,眉宇间透出几分沉静之气。见二人到来,起身拱手:“植兄,陆兄。”
植仪海笑道:“陆兄,此乃周怀安。怀安,此乃陆北顾。”
陆北顾连忙拱手:“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幸甚。”
周怀安微微一笑,道:“陆兄才名远播,我亦久闻。今日得见,实为幸事。”
三人落座,亭中清风徐来,茶香袅袅,气氛清雅。
“陆兄昨日听讲,可有心得?”周怀安开口问道。
陆北顾点头,道:“昨日宋先生讲《为政》篇,又忆起濂溪先生‘主静立极’之功,方知为政之道,始于修身。若心不静,志不坚,德不立,则政难行。”
周怀安目光一亮,道:“陆兄果然有悟。我亦曾读濂溪先生之书,深感其‘无极而太极’之说,实为理学之根基。心静,则理明;理明,则行正。此理若能贯通于心,便能以理应事,以德化人。”
陆北顾听得心中一震,道:“怀安兄所言,正合我意。我亦正欲深入研习濂溪先生之学,不知兄可愿共研?”
周怀安欣然点头:“正有此意。”
植仪海笑道:“好啊,今日得见二位志同道合,实为可喜之事。日后若能常聚,共研理学,切磋经义,必能相得益彰。”
三人相视一笑,心中皆生知己之感。
自那日起,陆北顾与周怀安、植仪海三人便常聚于国子监内,或于讲堂听学,或于亭中论道,或于书斋共读,彼此切磋,互为砥砺。陆北顾亦自此每日静坐,修身养性,格物致知,日日精进。
数日后,国子监举行一次经义策问,题目为《论为政以德》。陆北顾沉思良久,提笔而书,字字珠玑,句句精妙。他从《论语》入手,引《孟子》之言,结合濂溪先生“主静立极”之说,层层剖析,论述为政之道,始于修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文章一出,监中众人皆为之震动。宋堂颐阅后,亦赞曰:“此文理明义正,格物致知之功,已见端倪。陆北顾,可堪大器。”
此事传开,陆北顾之名,亦在国子监中渐起。
然而,学问之道,非止于文辞之工,更在于实践之行。一日,国子监外忽传边疆告急,西夏寇边,朝廷欲征募士子,前往边地协助军务。此事一出,监中众人议论纷纷,或言应征,或言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