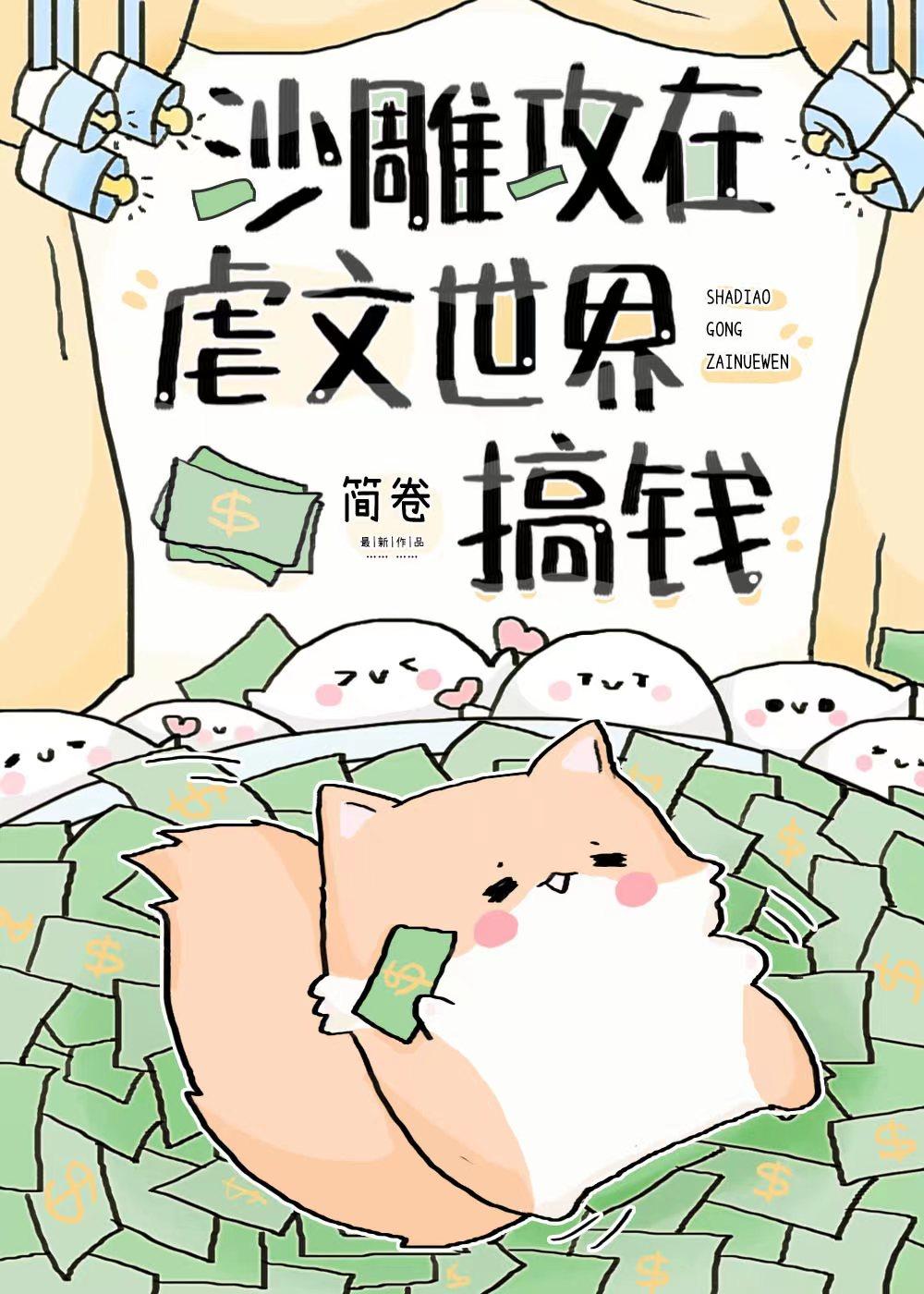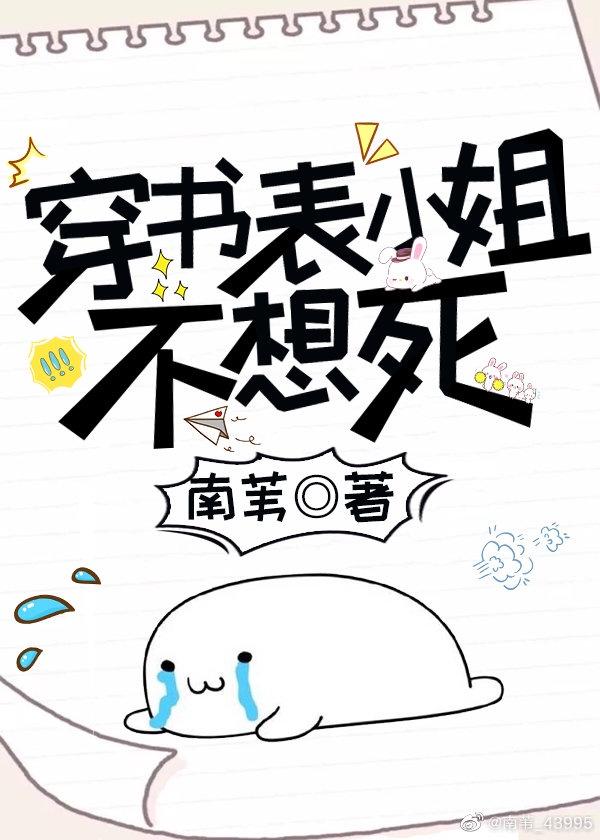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唐:我真没想当官啊 > 第141章 全都买国债了(第1页)
第141章 全都买国债了(第1页)
刘福贵今年五十五,老家在长安。隋朝那会儿,苛捐杂税多到离谱,家里田产全被嚯嚯没了。
再加上战乱不停,日子根本没法过。
没办法,他只能背井离乡,跑到陇右山区投靠亲戚。
大唐建立后,天下慢慢太平了,刘福贵就和亲戚合伙做生意。
他脑子好使,对市场行情那叫一个敏感,总能提前发现商机。
靠着这本事,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很快就攒下了万贯家财。
可年纪一大,思乡之情就像潮水一样,怎么都挡不住。
再加上和合伙人经营理念不合,矛盾越来越多,刘福贵一咬牙,分了家产,带着儿子、儿媳和小孙子,揣着五百两银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正月初九,一家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终于到了长安。
眼前的长安城依旧热闹非凡,街道上车水马龙,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可仔细一看,刘福贵发现长安和记忆里不太一样了,街巷布局、建筑风貌都变了不少,让他觉得有些陌生。
他先在西市的茶摊歇脚,让儿子去找牙人,打算租个院子住下来。
“这国债真有那么神?我咋感觉像骗人的呢!”
“可别乱说!《长安日报》背后可是陛下,天子还能骗咱们?”
“哪有买国债就能暴富的好事?说是朝廷借钱,又有点像做生意……”
“就是啊!难不成朝廷穷得叮当响,开始打老百姓的主意了?”
刘福贵本来没把邻桌的闲聊当回事,正准备端起茶碗润润嗓子,可“国债”“暴富”这几个词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
在商海里混了这么多年,他对商机的嗅觉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一听这话,刘福贵瞬间来了精神,大手一挥,喊道:“小二,这几位的茶钱我请了!”
众人先是一愣,然后赶紧拱手道谢。
刘福贵搬来长凳,大大咧咧地坐下,笑着说:“几位老哥,我刚从外地回来,啥都不知道,这国债到底是咋回事啊?”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国债的事儿大概说了一遍。
原来,朝廷为了西征吐蕃筹集粮草,推出了国债,老百姓买了国债,朝廷会在规定时间内连本带利还回来。
刘福贵越听越兴奋,鼻翼不自觉地动了动——这是他发现商机时的老毛病。
“老哥,能把报纸借我看看不?”
“说啥借啊!您请我们喝茶,这报纸就送您了!”
刘福贵接过报纸,也顾不上客气,迫不及待地翻起来。
他眼睛死死盯着国债的报道,那些八卦奇闻、志怪连载啥的,根本入不了他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