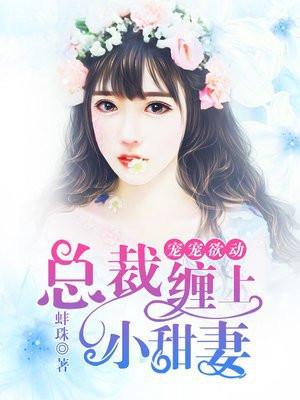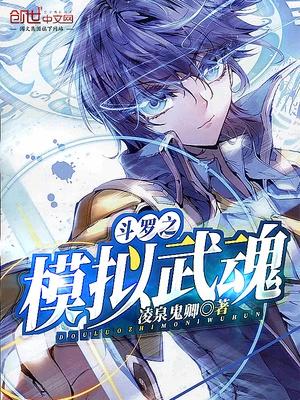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红楼之黛玉长嫂 > 203第 203 章(第2页)
203第 203 章(第2页)
三、毕业之时,每人须完成一件“益民事”??无论是修桥、制药、绘图,还是创办夜校,皆可。
首批二十名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混血少年,父亲是波斯商人,母亲是扬州船工之女。他天生卷发碧眼,从小被称作“胡鬼”,屡遭欺凌。但他精通算术,竟能用沙盘推演潮汐规律。霍七娘让他主理“天文水利课”,并鼓励他说:“你的血统不属于任何一方,但它属于整个天下。”
春深时节,书院后山桃花盛开。霍七娘带学生们登山采药,讲解草木性味。途中,梅初雪悄悄递给她一封信,是沈素衣派人快马送来的。
信中写道:
>“近日朝中拟议‘全民启蒙法’,欲将边隅启蒙所制度化,覆盖全国每一州县。然保守派仍阻挠‘女子可任县令’条款,声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柳青鸾怒斥其荒谬,当场出示敦煌新出土简牍??汉代已有女啬夫执掌乡政,文书确凿。太后最终拍案定谳:‘既古已有之,何言悖逆?’法案有望五月施行。
>另,甘州女子武塾学员林小娥(与忠魂同名)率队巡边,击退劫匪,救回被掳百姓十七人。捷报传来,军中皆呼‘巾帼再起’。
>你送去的《薪传录》摹本已交国子监编修局,或将收入新编《女子文集》。紫绡若在,必含笑九泉。”
霍七娘读罢,仰望苍穹。云卷云舒,恍若当年四卿并肩议事于宫城之巅。那时她们也曾被人讥为“牝鸡”,可如今,连国史都要为她们腾出一页。
下山路上,她对学生们说:“你们以为读书是为了考试做官?错了。读书是为了不让别人替你决定你是谁。一百年前,林先生写下理想;三十年前,我们拼命让它成真;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要让它永不熄灭。”
回到书院,已是黄昏。梅初雪正在教几个小女孩用芦苇笔写字。她们在地上铺开宣纸,一笔一划写着:“我叫阿莲,我要当医生。”“我叫翠姑,我要回家盖房子。”“我叫小雪,我要把《薪传录》读完。”
霍七娘站在廊下,静静看着。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夜里,她独坐灯下,提笔给沈素衣回信:
>“《薪传录》已交学生誊抄,盲文版亦在筹备。拾遗精舍本月已收三十七名新生,最小者六岁,最大者四十有二。昨有寡妇携幼子而来,言愿终身在此teaching,只求孩子不再被人唤作‘无父之种’。
>我知新政仍有反复之忧,豪强未必真心臣服,宗室暗流仍在涌动。但你看,当千万普通人开始为自己说话时,谁还能堵住他们的嘴?
>记得老师说过:‘变革如种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播下的不是法令,是人心。
>请转告长安诸君:不必担忧我年迈归隐。我在江南种下的,不只是书院,是一颗种子。它会生根,会开花,会在某一夜风雨后,突然长成一片林。”
写完,她吹熄蜡烛,推开窗户。月光洒满庭院,照在那架已组装成功的水力磨坊上。水流缓缓推动轮轴,发出轻柔的吱呀声,宛如时光前行的脚步。
她低声念道:“原来这条路,早就有人走过……”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一阵笛声。是那位盲女在练习新曲,旋律婉转凄美,竟是《葬花吟》的调子。霍七娘闭目倾听,忽觉心头一暖。
花落了,还会再开;人走了,光还在。
翌日清晨,书院门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塾师,手持戒尺,满脸严肃;另一位则是当地县令的幕僚,穿着体面,神情倨傲。
老塾师一进门便大声质问:“霍七娘!你私设学堂,收纳畸零之人,教授非正统之书,可知犯了教化之禁?此等胡闹,岂能长久!”
霍七娘正在指导学生测量日晷投影,闻言抬起头,神色平静:“请问老先生,何为‘正统之书’?若《女诫》是正统,那为何千年来女子仍被卖作妾婢?若《四书》是正统,那为何天下饥民仍不知赈灾条例?”
老塾师语塞。
那幕僚冷笑:“你纵有军功,也无权擅自办学!县衙未曾备案,经费从何而来?学生出路在哪?莫不是蛊惑人心,聚众滋事!”
霍七娘起身,拍拍衣袍尘土,淡淡道:“我的经费来自民间捐赠,每一笔都有账可查;学生的出路,在于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至于备案??你可知道,朝廷三月下诏,明令各地设立‘拾遗类学堂’,专收边缘孩童?文书已在路上,半月即达。你回去问问你们县令,是要顺应新政,还是等着被参‘阻挠启蒙’?”
两人脸色骤变,悻悻而去。
当晚,霍七娘召集全体师生,在院中燃起篝火。她将那份朝廷诏令的抄本投入火中,火焰腾起,照亮众人面容。
“他们怕我们,是因为我们打破了规矩。”她说,“可谁定的规矩?是那些从未饿过肚子、从未被人踩在脚下的人。今天我们烧的不是法令,是枷锁。从今往后,这里不叫‘私塾’,也不叫‘精舍’,我们就叫??**破规堂**。”
孩子们齐声欢呼。梅初雪站在人群中,手捧《薪传录》,眼中泪光闪烁。
火光映照之下,屋檐下的“续明”灯笼愈发鲜亮,仿佛预示着:黑夜再长,也挡不住一点不肯熄灭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