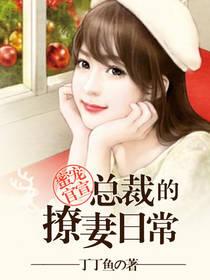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零四章 示警太子(第1页)
第一千二百零四章 示警太子(第1页)
此言一出,殿中百官哗然。朱元璋眼神微动,淡淡道:“你是想将你王叔送走?”朱标不卑不亢:“儿臣非逐贤,乃惧流言;非弃柱石,乃求正统。”朱元璋沉吟不语,忽而大笑:“好个‘惧流言’,好个‘求正统’。你这一步,是要自立旗号?”朱标低首不语,只拱手肃立。半晌,朱元璋笑意渐敛,缓缓道:“准了。”“着王爷赴南部督府,掌南镇兵事,六月启程。”王府中,朱瀚看着黄祁呈来的圣旨,脸上不悲不喜。“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王爷,您当真离京?”黄祁不舍。“你说我走了吗?”朱瀚瞥他一眼,“我不过是将目光移开一寸,让他露出锋刃。”“你留京。”“你盯住朱棣,看他下一步,是觐见,还是出京。”黄祁肃声应诺。而在皇城东南角,朱棣披衣而立,眸中却透出一丝躁意。“王爷。”杜湛轻声,“王爷之议,是否可定期启行赴北营,以振兵心?”朱棣沉声道:“不急。”“可朱瀚已要远调,东宫又初立……”“越是如此,越不能轻动。”他转身望向城西,“朱瀚……不会真走。”“可若他真走了呢?”杜湛试探。朱棣眸中寒光一闪:“若他真走,便是……我登场的时候。”他缓缓抬手,指向苍穹:“这天,久矣未换。”系统提示闪现:【剧情推进:设局三策·困燕王】【燕王谋动度-10,东宫稳固度10】【奖励触发:获得“东宫内卫密谍权”】朱瀚合卷于灯下,望着系统浮标,轻叹:“朱棣,你以为我退了,便没人挡你。”“你错了。”“朱标已非当年少年。”京城四月,杏花尽落,南风徐徐,万象更新。但在这一片春意中,皇宫西偏内的一座密室,却笼罩着不同寻常的寒意。朱瀚已启程南调之令将至,消息一经传出,朝堂震动,甚至连三法司之首也接到了“观察燕王府”的密令,虽然未署名,却清晰如刀。朱棣自王府中连日未出,至第四夜,终于披甲夜骑,北上操营。他没有上奏,也未申告,仅以“夜巡兵营”为由,带五十甲士出燕王府,悄然出城。次日清晨,朱标披朝服步入朝堂,脸色如常,却眼神锐利如冰。杜世清上前,低声禀道:“殿下,朱棣出京,未申旨。”朱标微一点头:“预料之中。”顾清萍随后而入,手中递来一份折本:“昨夜东营校场有异动,四更前有百人集合,皆身披重甲,未挂番号。”朱标将折子合起:“传我令,东宫设议狱于千策堂下,召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三方之首,令其连署署权,设‘春察制诏’。”杜世清微惊:“殿下是要启‘诏狱’?”朱标平静道:“非诏狱,而是议狱。”“非为断罪,而是为立规。”顾清萍凝视他片刻:“你是要用律法将皇权之下的兄弟之争,转为体制之内的纲纪约束。”朱标笑道:“皇叔教我,握剑者不可手软。但我知道,真正的帝王,不只用剑,还要立尺。”“今日之后,便是我朱标第一次动用律法之威。”朝臣哗然,王府惊动,朱棣北营即刻收到风声。“太子要审我?”朱棣捏紧折子,眸光如霜。陶慎面色阴沉:“不明指名,却单设议狱,且三道连署,刑、察、缇骑共举,这分明是……引你犯身。”朱棣冷笑:“他以为我怕?”“他不知,我朱棣纵无兵权,也不做他阶下囚。”千策堂前,朱标步下台阶,目光落在京郊那条通道上。杜世清在侧,声音低沉:“他来了。”朱标点头,沉声道:“门开一尺,不是为了迎王,是为正法。”顾清萍肃容站在朱标身后,低声道:“今日之局,殿下立一尺之法,朱棣若踏过,便是天子法前,王不能免。”朱标深吸一口气:“走,我们入堂。”与此同时,王府密室内,朱瀚已至南郡,却并未离开部署核心。他坐于画舫上,望着飞鸽传信入笼,展开一看,不觉露出一丝笑意:“朱标终于动手了。”黄祁在侧:“王爷,燕王今早启程回京,据探子所言,身侧仅两人,无兵不从。”朱瀚轻叹:“他这是赌一口气。”黄祁问:“他会否在朝中翻盘?”“不会。”朱瀚语气平静:“朱标若未立议狱,他或可先手;但既已设局,便是请君入瓮。”“接下来,是朱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压制兄弟’——他要赢得,不是皇兄的心,而是天下人的眼。”黄祁肃然:“王爷,我们是否仍要回京?”朱瀚淡淡一笑:“我不回,他更自在。”“我不在,他更无惧。”,!京城,议狱开审。朱棣步入堂内,披王袍,未带甲,身后仅陶慎与杜湛两人。朱标坐于正席,未着冠冕,仅披青衣,身后顾清萍、杜世清分列左右。“殿下。”朱棣站定堂下,眼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冷意,“今日之审,太子要我认何罪?”朱标平静望着他:“无罪可审。”朱棣一愣。“议狱,不是审你,是审规矩。”朱标一字一句,“你夜离京、擅入北营、动重甲、未申奏,这四事,非谋非乱,但皆违礼制。”“你是王,是父皇之子,你有你的尊荣。但我,是储君,我有我的守正。”“今日你来,是你愿入议狱。”“而今日之后,你出,是因为你服法。”朱棣凝视他许久,良久点头:“好,好一个‘议狱非审’,你朱标,终究不再是昔日懦弱之子了。”“但你记着,朱瀚还在。”“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朱标缓缓站起,目光坚定如炬:“正因如此,我才立议狱。”“我不求独权,但求众心。”“你可以不服我,但你不能不服这法。”朱棣怔在原地,片刻后,终于低头,轻声道:“臣弟,领旨。”王府书房,黄祁手执密报,道:“王爷,衡衡宫修缮已近完工,太监程守义进出频繁,内中调入两位不属司礼监编制的新宫女,据查皆无过往档案。”朱瀚眉头微蹙:“衡衡宫?那是何人主意?”黄祁答:“据查,此事并非内务监主导,而是由皇后口谕提出,说是‘陛下宿念旧地,意欲重启讲读之所’。”“皇后口谕?”朱瀚轻声念道,眼中闪过一丝幽深,“旧地、讲读、文案……皇兄这是要为谁预留一室讲席?”黄祁问道:“是为太子?”朱瀚摇头:“若真为太子,用不着避开东宫通令;若是为旁人……便只可能是那位四皇子。”“朱棣。”黄祁低声道。朱瀚缓缓放下手中茶盏,语气淡然中却夹着寒意:“朱棣虽刚受议狱,已然收势,但皇兄未有责罚,反命其静观衡衡宫重修。你觉得这像是什么?”黄祁沉声:“像是在留路。”朱瀚点头:“不错,是留一线,也是试一线。”“皇兄未尝不知朱标之坚,也未必看不清朱棣之锐。可他……终究仍要‘两备’。”黄祁问:“王爷要不要插手?”朱瀚轻轻一笑:“若我插手,反倒显得我在忌惮朱棣。”“这一步棋,不该由我下。”“应该由太子亲自回应。”与此同时,东宫书阁内,朱标静坐案前,一纸密报静静摊开,顾清萍拈香煮茶,将一盏香茶推至他手边。“殿下,衡衡宫之事,您怎么看?”她轻声问道。朱标目光淡然:“这是父皇给我的一道题。”顾清萍轻声道:“若您不应,便是默许;若您先动,反成小气。”朱标道:“所以我不应,也不动。”顾清萍一怔:“那……”朱标抬起眼眸,平静却坚定:“我派人修缮‘建德堂’,取自‘建国安德’之意,设太学讲席,召京中学士、进士、监生论讲于此,名曰‘储学问政’。”“父皇借衡衡宫试我是否忌惮朱棣,我便以开堂施教之名,告天下——我不怕。”“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不怕,我还要做给他看:朱标,能坐东宫,不靠宫门之争,只凭问政之实。”顾清萍望着他,眼中浮现欣慰:“这步棋走出去,天下尽知,太子之学、太子之政、太子之胸襟。”“那衡衡宫再起,也无人敢再言争储。”建德堂设于东宫南苑,规模不及千策堂宏伟,却因其“学讲之名”引起士林关注。四日后,朱标亲自主持开讲,首议《春秋公羊传》,集儒生之言,论“义统”与“礼治”,言中不避储君之位,落字皆是“身负大统,不离礼纲”。当日之后,建德堂文稿流传朝中,翰林院、国子监皆来求观,东宫声望更上一层楼。朱瀚得讯后,淡淡而笑:“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回应,从来不是争锋,而是正道。”“朱棣若有心,还能学会自守。”黄祁却低声道:“可惜……燕王不肯学。”“他今晨秘密召杜湛、陶慎等旧将入府,虽未调兵,却似已有不安。”朱瀚眸中微沉:“他若再动,朝局便乱。”“是时候,再‘敲打’一次了。”当天夜里,朱瀚命黄祁秘密拜访燕王府。此去非为夺权,不为逼退,而是当面对话。朱棣府中,灯火幽暗,朱瀚一身常服,步入偏厅,朱棣独坐灯下,眼神复杂。“皇叔大驾,孩儿未曾预料。”朱瀚笑道:“你我之间,还需‘驾’与‘礼’么?”朱棣抿唇不语。朱瀚落座:“衡衡宫之事,我不管,建德堂之策,我也不劝。但我只问你一句——你如今若登位,你打算怎么做?”,!朱棣一愣,脱口而出:“我自能守国律、定大纲,安百官!”朱瀚摇头,盯着他:“错。”“你想的是胜朱标,不是胜天下。”“你要想坐那龙椅,靠的不是击倒兄长,而是服众百官,安天下心。”“你要是不明白这点,这一生,你都只能是一个‘王’,不是‘君’。”朱棣动容,却仍咬牙:“可父皇一直留我一线,我为何不能争?”“因为你不该争。”朱瀚起身,背手而立:“有些位置,是你注定走不到的;有些人,是你永远比不上的。朱标不是靠我,也不是靠皇兄,是靠他自己走到这一步的。”“我今日来,不是压你,不是警你。”“是劝你。”“别再失去你最后的分寸。”朱棣眼中闪烁,良久低声道:“孩儿……明白了。”朱瀚立于王府庭中小亭,一袭单袍,端茶于手,目光却始终落在案上那几页飞骑急递而来的密报。“王爷。”黄祁走入,低声禀道,“吏部侍郎韩允、户部主事周望连日频至国子监讲舍,暗中接触建德堂诸讲学之士。”朱瀚轻抬眼:“接触讲士?意欲何为?”黄祁答道:“韩允素与礼部尚书刘广不睦,恐其趁机拉拢士林,意图在下科进士荐举中插手太子堂中之人,以为羽翼。”朱瀚冷笑:“这等人倒是比燕王更狡。”“朱棣尚知权谋不可明争,而这些自诩清议之人,却将士林当作羽翼,将讲堂当作驿站。”“他们想借太子的势,养自己的名。”黄祁道:“是否要立刻示警太子?”“不急。”朱瀚轻抿茶水,“东宫建德堂开讲,本是太子自立之局。他要学会布阵、也要学会拔刺。”“让他自己察觉,自己处理。”“若他连这一点都办不到,那他便还不配坐稳东宫之位。”黄祁低头应是,却又迟疑:“王爷……若此事蔓延,恐有官评流转,牵连士林与朝议。”朱瀚却忽然一笑:“你放心,朱标比你想得更清醒。”建德堂讲席,今日所议为《尚书·洪范》之“大中至正”,台下诸士皆聚,朱标居于高座之上,着素青衫,神色沉稳。“诸位。”他朗声开口,“大中者,权衡之道也;至正者,行德之本也。”“若学识之士只知趋势、附势,而不思明道守正,那即便列名朝列,也不过是附骨之蛆。”:()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