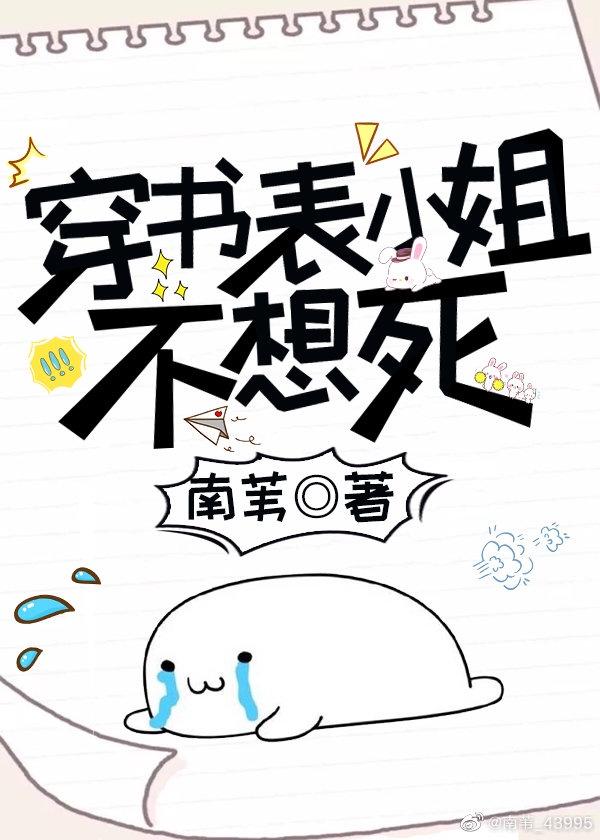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蓝锁】出走王子后日谈 > 笛鸣白鹿巷(第2页)
笛鸣白鹿巷(第2页)
是门将谢伊。他站在遥远的己方禁区线上,双手同样夸张地拢在嘴边,模仿着玲王刚才的姿势大喊:“需要我弃门而出,同时抱住你们所有人吗?!目前看来,只有我的臂展最适合干这种事了!但要快点儿决定,万一他们趁机快发中场球呢?!”
他们互相拉扯着,搀扶着,从雪泥里站起来,每个人都脏得不成样子,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惊人。玲王被汤姆和利亚姆一左一右架着胳膊,伯顿用力揉了揉他们每个人的头发。
远处,谢伊满意地看着这一幕,放下拢在嘴边的手,耸了耸肩转身拍了拍自家的门柱:“看,他们不需要我,咱们守好这儿就行。”
补时只有四分钟,热刺的球迷却陆陆续续开始退场了,似乎对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反杀并无信心,而事实果真如此。
先是零星几个。靠近通道口的位置,有人默默站起身,将白色的围巾从脖子上解下,团在手里,低着头快步消失在出口的阴影里,不愿多看一眼场上的结局。他们的动作很轻,但在周围依然端坐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像雪原上最早融化的几处斑驳。
主裁判将哨子含在嘴里,看了看表。
热刺球员发起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长传冲吊,
足球在空中划过一道漫长的抛物线,还未落地。
“哔——哔——哔——!!”
清脆、响亮、终结一切的三声长哨,比赛结束。
玲王站在原地长长地彻底地吐出了一口气,白色的雾气在眼前散开。紧绷了九十多分钟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可以稍微松弛,膝盖的刺痛和全身透支般的疲惫就重新涌起。
他抬起头看着阴沉的天空,细雪不知何时已完全停止。白鹿巷的下午,在主场球迷大片提前退场留下的空白座位映衬下显得格外空旷和寂静。只有那一小团鲜艳的红色在场地中央聚集拥抱,像是这片苍茫灰白中唯一顽强燃烧的火焰。
玲王闭上眼,听着耳边越来越近的,属于自己人的欢呼与笑声。
赛后,尼尔·班菲尔德教练双手抱胸靠在更衣室门框上,看着他的球员们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带着满身的汗水和亢奋过后的虚脱。大部分人都直接瘫倒在长凳上,或仰头灌着运动饮料,还在语无伦次地重复着比赛中的某个瞬间。
然后他看到了御影玲王。那个孩子走在队伍偏后的位置,眉头微蹙,脚步异样。等玲王走到自己储物柜前开始费力地地弯腰解鞋带时,班菲尔德走了过去,阴影落在玲王低垂的头顶。
“Mikage,怎么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吗?”教练的声音不高,压过了更衣室里的嘈杂,“中场的时候就觉得你有点奇怪了。”
玲王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自己的膝盖,像是才注意到它的抗议:“抱歉,教练。刚才太兴奋了,完全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啊?这句话让班菲尔德叹气,他太了解这些年轻的球员,尤其是像玲王这样心高气傲的。他们能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只要大脑被更强烈的目标所占据。
班菲尔德本该生气。气他不爱惜身体,气他隐瞒伤情,气他在如此重要的成长阶段可能因小失大。他张开嘴,那些责备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关于职业素养,关于长远规划,关于对球队的责任。
但是看着玲王依旧挺直的背脊,班菲尔德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完全无法像平时一样出言责备他不冷静。这个孩子太优秀——也太卖力了。他于是伸出手,用力拍了拍玲王的肩膀。
“下次有任何不对,立刻告诉我。”教练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清,“你的感觉很重要,明白吗?不止是对比赛,对你自己的未来更重要。我们都想看到你的未来,所以对自己更负责一点……不管是在这里,还是以后在其他队伍。”
“我明白,教练。抱歉。”他知道班菲尔德今天说了太多不该说的了,作为阿森纳的预备队教练,他实在不该有超越球队立场的建议。
又是道歉,班菲尔德扶额,为什么自己手底下这群日本小孩全都一个样子?遇到问题道歉先行,哪怕是他是御影玲王。
“队医马上过来给你检查,好好配合。今晚不许参加任何庆祝活动,立刻处理,这是命令。”
“是。”
班菲尔德又看了他一眼,这才转身去处理其他事务,但目光仍时不时扫向那个角落。
玲王看着教练走开,才慢慢,慢慢地松懈下一直挺直的背,更清晰地感受到膝处一波波涌上的的钝痛。他低头小心地卷下湿透的球袜,露出膝盖。皮肤表面看起来并无严重异样,只是有些泛红,但当他尝试轻微弯曲时,疼痛让他瞬间停住了动作。
好吧,看来是在蓝色监狱集训了一年都没有受过什么伤的缘故,让自己误认为全天下人都有那样一副钢筋铁骨。不过御影玲王完全不后悔——他是绝不会放过自己的那种人。如此优越的身体和完美的头脑理应被最大限度地使用,否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
明天会有诊断,会有报告,会有决定。
但今夜只有雪,只有沉默,只有凯旋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