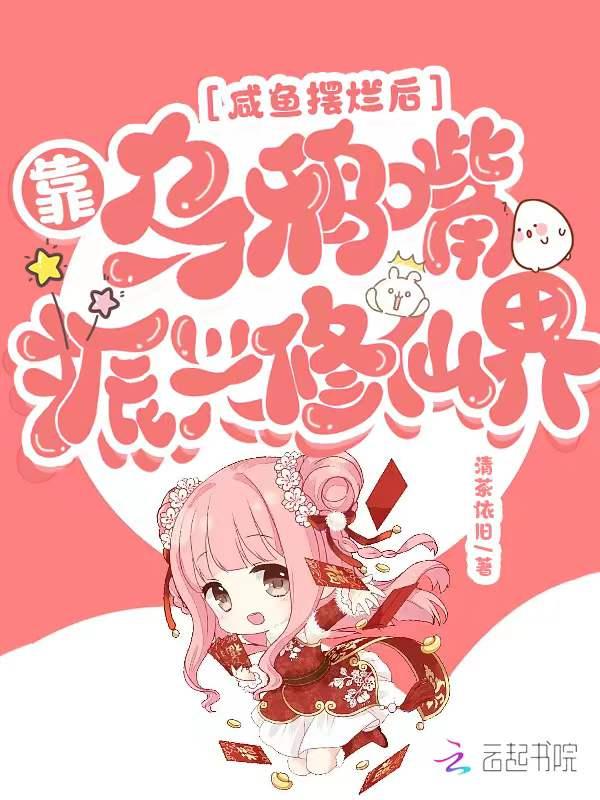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重生之京华无雪 > 漏网之鱼(第2页)
漏网之鱼(第2页)
再后来时,便是听见山下的农户们上山砍柴闲谈,说一黑衣剑客夜闯那狗官府邸,将其一家老小杀了个精光。
据报官的打更人说,那天夜半三更,经过那座府邸时听见“嗬嗬”的声音,他心下不安,透过门缝一瞧,见那狗官跪在剑客面前,手捂着脖子,血一股一股地往外冒,院子里血气冲天。
那剑客似是察觉到他,回头一看,冷若冰霜,犹如恶鬼,吓得他拔腿就跑,半路上遇见巡逻的卫兵,连忙说了这事,待他们赶到时,剑客早已不在,只余下一院子横七竖八,死状惨烈的尸首。
小姐听见这件事,对她说那黑衣剑客估摸着就是她们救的那人。
她吓了一跳,正庆幸这人幸好早走了,没想到回去后看见一个黑衣人影背对着她们站在门口,听见动静他回过头,还没来得及紧张,忘忧就看见这人掀袍朝小姐跪了下来。
“广风这条命是小姐救的,如今大仇已报,牵挂均已不在世间,愿做小姐的剑,任凭小姐差遣。”
后来他便留在了山上,时不时教授小姐武学,更多的还是往来于阗京城和晖云山之间,帮她查探消息。
上个月广风循着这些年查到的千丝万缕的消息,说他怀疑当初的狱卒还没死全,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可能躲在什么地方。
为此,他当即动身去了外地一趟,看样子是刚刚回来。
广风只点点头,忘忧也习惯了他惜字如金的性子,拎着茶壶推门出去了。
“您怎么不从门进啊?”
“门口有人。”
隋垂容了然,她点点头,念竹手巧,府上的小丫鬟全来找她学着绣花样,每天一到这个时辰,院里叽叽喳喳,尽是小女孩的笑声。
忘忧泡好茶水送了进来便径自出去找念竹了,隋垂容给广风倒了杯热茶,迫不及待问道:“风叔,有消息了吗?”
“当年有个狱卒叫任大飞,他是一众狱卒的头子,他之前有个相好的,是东街粮油坊掌柜的小女儿。本来二人已经订下婚约,可那任大飞突然失踪,这姑娘便干脆利索改嫁了他人。
我打听到街坊邻居都说这二人感情十分要好,如此干脆改嫁,实在令人起疑。正巧那天那姑娘带着陪嫁丫鬟出门,我便偷偷跟了上去,佯装认识任大飞,给她扔了个纸团。”
广风顿了顿,拾起热茶喝了一口,继续说道。
“那姑娘一打开纸团,面色一下子变得喜忧参半,我与她二人在酒楼雅间坐下谈话,那姑娘问我‘飞哥还好吗?他身体怎么样?换了个地方生活可适应得来?’,我随意打了几个马虎眼搪塞了过去,那姑娘竟也没怀疑,可见二人也许久没见了。”
广风重重放下茶壶,“我假装任大飞的朋友,说来阗京做生意顺便帮他探望一下你,那姑娘久处深闺,天真无邪,几下便套出了不少话。”
“这才知道任大飞竟然没死,他当年趁乱跑掉,临走时偷偷见了这姑娘一面,将攒的金银细软分了一半给她,让她保密,再找个好人家嫁了,他估摸着这辈子都不会回阗京城了。”
“原来如此,现下可查出那人在哪藏着了?”隋垂容按耐下激动,冷静开口,要扳倒许邱德,这人不可或缺。
广风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说任大飞行踪不定,隔一段时间便要换一个地方,问那姑娘可知当初任大飞临走时与她说他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可那姑娘也不知道。只说任大飞从前和她说过,他喜欢有水的地方。”
“水?”隋垂容喃喃道,“金陵?邵阳?还是江南…”
“我已查过不少地方了,都没有。不过我在邵阳有个朋友,他传信同我说,他好像看见过我画像上的人,所以我准备动身去邵阳看看,十有八九人就在那,不过我也不敢打包票,得去看了才知道。”
邵阳……
隋垂容失神片刻,竟然是那里。
“好,风叔你一路小心,切莫注意自己安全,路上的盘缠可还够?”
隋垂容拿出几张银票递给广风,广风摇摇头,“够,小姐不必给我。”
“此去路远,万一有什么突发事,多点银钱好傍身,我也能放下点心,您就收着吧风叔,您还是我半个师傅呢,跟徒弟客气什么!”
隋垂容眨眨眼笑道,在熟悉的长辈面前,她总会不自觉露出调皮样。
广风无奈接过,脸上疤痕瞬间柔和了许多,他感慨道:“许久不见小姐,感觉小姐爱笑了许多。”
“啊,是吗?”隋垂容愣了一下,垂眸看向鞋上镶嵌着的珠子,“许是最近顺利,心情好吧。”
广风欣慰点点头。
他当初一见隋垂容,便觉得这姑娘眼底有与他一模一样的东西,是深仇,也是积恨,虽也好奇她一个小姑娘怎么有如此情绪,但他生来冷漠,不喜欢多问闲事。
隋垂容救了他,让他有机会能报仇雪恨,于他可谓有救命之恩。
最开始他只想做一把称职的利刃,结草衔环,如果运气不好死了,刚好能去找他的妻子。
可这么些年,早已将她当成了半个女儿,看见她单薄的肩膀上扛了许多沉重包袱,总会心疼她不容易。
是以,看到隋垂容现在情绪真的愈来愈好,他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