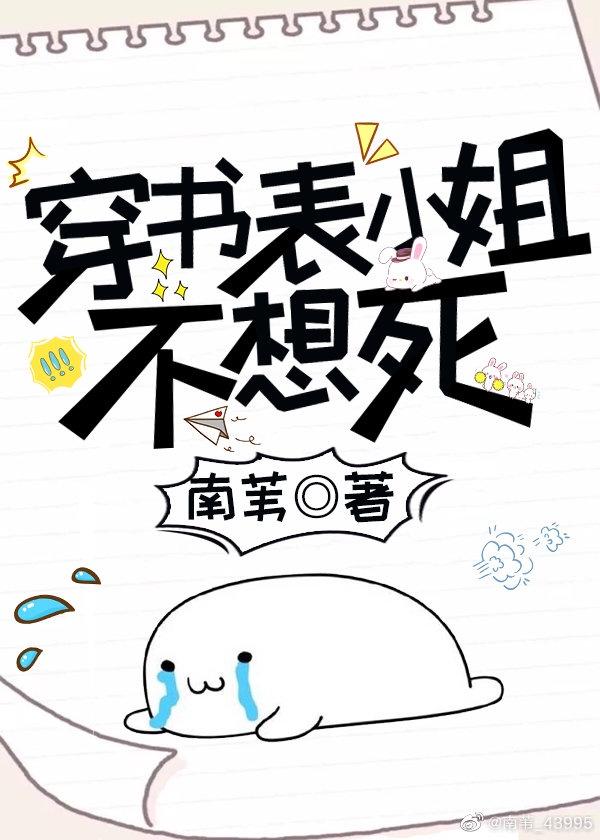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红楼芳华,权倾天下 > 第196章 大官人回来了(第3页)
第196章 大官人回来了(第3页)
傅账房只觉得心口那只老鹿都快撞碎了腔子跳出来!
自家东家竟一步登天,成了五品朝廷命官!这清河县的天,从今往后,怕是要姓西门了!那街面上的石板,明日都得跟着改换颜色!
大官人坦然受着二人的跪拜。他抬手虚扶了一下:“起来吧,自家铺子里,不必如此大礼。”
徐直和傅账房这才颤巍巍爬起来,脸上兀自带着做梦般的狂喜。
徐直捧着那文书,爱不释手,目光又扫到另外两卷规制图样,好奇道:“大官人,这…这七品和九品的服色规制是……”他心念电转,猜测着可能是给哪位亲信谋的差事。
大官人略一偏头,目光投向身后侍立的来保和玳安,淡淡道:“喏,穿在身上的主儿,不就在这儿么。”
徐直和傅账房顺着大官人的目光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来保?玳安?一个西门府上的官家,一个平日里鞍前马后跑腿听唤、在府里地位不上不下的贴身小厮?
一个七品,一个九品?
两个都是官身了?
这哪是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简直是西门大官人把天捅了个窟窿,连带着脚底下的鸡犬都沾了仙气,直往云霄里窜!
这泼天的震撼,比方才得知大官人升官,更似两记闷棍,结结实实夯在徐直和傅账房的天灵盖上,砸得他俩眼前金星乱迸,耳朵里嗡嗡作响!
两人反应也是极快,刚刚站直的身子,立刻又“噗通”、“噗通”跪了下去,这回是朝着来保和玳安,口中连呼:
“恭喜来保老爷!贺喜来保老爷!七品前程,青云直上!”
“恭喜玳安老爷!贺喜玳安老爷!九品官身,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啊!”
来保和玳安此刻早已挺直了腰板,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嘴角咧到了耳根。
来保到底是老成些,强压着心头的狂喜,故作谦逊地摆摆手,声音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响亮和底气:
“哎哟!徐掌柜、傅账房,快请起,快请起!折煞我们了!什么老爷不老爷的,我和玳安,说到底,给咱们家大爹跑腿办事的下人!这点子微末前程,全是托赖大爹天高地厚的恩典!没大爹抬举,我们算个什么?”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满脸堆笑、眼中却难掩复杂与羡慕的徐直和傅账房,慢悠悠补了一句,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两人心上:
“我兄弟二人今日之微末前程,焉知不是二位掌柜的明日之阶?尽心给大爹办事,前程自有大爹抬举!”
这话一出,徐直和傅账房心头俱是一震,如同醍醐灌顶!
是啊,来保自不必说,连玳安都能一跃龙门,自己若忠心办事,何愁没有前程?
两人眼中瞬间爆发出无比热切的光芒,连连点头哈腰,口称:“是极!是极!来保老爷金玉良言!小的们定当肝脑涂地,绝不敢有半分懈怠!!”
玳安正洋洋得意,挺着刚有了官身的细腰杆子,也想学着来保的腔调说几句场面话,显摆显摆。
谁知话头刚滚到嗓子眼儿,大官人反手就是一记“刮子”,带着风声,“啪”地一声脆响,结结实实甩在他后脑勺上,打得他脖子一缩,那点子得意劲儿瞬间烟消云散。
“聒噪!”大官人眼皮都没抬,不耐烦地斥了一句,“好了,都别杵着了,起来吧。”
他目光如电,猛地钉在徐直脸上:“徐直,听真了:官服规制、尺寸,一丝一毫都在这文书里。你,立刻!去把铺子里那几个老裁缝,给我从被窝里揪出来!点上通宵达旦的灯烛,备齐最上等的贡缎、金线、银针!”
“今晚!就算把眼珠子熬瞎了,也得把这三套官服给我赶出来!针脚要密,补子要活,一丝儿差错都不许有!”
“明儿一早,天蒙蒙亮,”大官人伸出一根手指,几乎戳到徐直的鼻尖,“我要看到这三套官袍玉带,整整齐齐、分毫不差地摆在老爷我面前!听见没有?!”
徐直一听,这关乎东家和新晋两位“老爷”明日的体面,更是关乎自己脑袋在脖子上安稳不稳的大事,哪里还敢喘半口粗气?
他“噗通”又跪下,把胸脯拍得如同擂鼓:“老爷放心!咱们铺子就是吃这碗官服饭的,熟门熟路,小的今晚就钉在铺子里,眼珠子一眨不眨盯着!保管明儿一早,妥妥帖帖、恭恭敬敬送到您老案头!”
“嗯!”大官人鼻腔里哼出一声算是应了,不再多言。
带着来保与玳安,袍角带风地出了绸缎铺。
西门大官人领着来保、玳安,一路意气风发,马蹄嘚嘚回到府门前。
早有那伶俐的小厮,撒丫子飞跑进去,扯着脖子,声音尖利得能划破夜空:“老爷回府喽——!老爷回府喽——!”
这一嗓子,活像滚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整个内宅“轰”地一声就炸开了锅!
月娘正歪在暖炕上,就着明亮的烛火翻看账册,闻言心头一跳,忙将手中册页一合,拢了拢一丝不乱的鬓角,脸上瞬间堆满喜色,趿拉着软底鞋急急就往外迎。
那厢房里,潘金莲正对着菱花镜描眉画鬓,李桂姐和香菱几个在廊下磕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
听见动静,一个个脸上如同变戏法似的,霎时堆起十二分的欢喜,莺莺燕燕,环佩叮当,簇拥着月娘,脚步匆匆,直往仪门处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