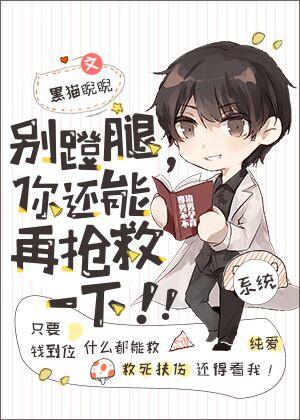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双玉记 > 第204章(第2页)
第204章(第2页)
他甚至在脑子里给白玉山演绎了一场生动活泼的“赵版曲水流觞”:
“此时朝我们流过来的是太祖陛下,太祖陛下壮年病亡,请大家为他悼诗一首;刚刚飘过去的是高祖他老人家,老爷子飘的很安详,嘴角还带着笑……”
白玉山:“……别疯。”
他短暂地将伊珏颇为狂躁的意识压制住,自己控制着这副身体抓住绳梯缓缓下落,还有余力从暗囊里取出一只枣核大小刻了符阵的木鸟,激活阵纹让木鸟带话去找长平,调兵围住整条山脉。
本该手忙脚乱,他却举重若轻,离地三尺时松开手,双脚落在松软土层上无声无息。
落地时顺便将意识海里的伊珏推出去,自己退回意识深处,不解地问:“何至于此?”
伊珏没说话,踩了踩脚下的土地,确认潮气还未严重到一脚能跺出水坑,松了一直悬着的心。
许久才回答他:
“因为我打算这辈子死时躺到你的棺里去。”
玉枕蒙了尘,却未朽坏,还能让他躺上去,枕在赵景铄枕过的枕上。
然后在那座已经衰败的陵里腐朽零落。
让尘归尘,土归土,属于赵景铄的,归还赵景铄。
地穴里寂无人声,却隐约有光。
有光就有风,有风意味着或有地下暗河,或另有出口。
伊珏贴着墙壁借着浓重阴影,缓慢地向前探,微弱的风随着他越走越近,带来丝丝缕缕血腥的气味。
新鲜血液聚集多时,腥味浓重,使人欲呕。而腐败变质的血凝聚过多,却是格外的臭。
腥臭的气味被风卷入鼻息,伊珏顿了顿,弯下腰一步一步将自己掖进阴影里谨慎地往后退——等长平带军来援。
白玉山挑起眉:“我以为你会往前冲。”
伊珏说:“我在你心里有多蠢?我疯了?”
“你在我面前很少带脑子。”
白玉山说着沉吟片刻,才恍惚记起他也是领过虎符镇守一方的将领,悍勇之外不乏谋略,但是:“我总觉得你这‘子虚’活不长。”
伊珏倒也不否认,能将该做的事做完,该还的债还清,他区区“子虚”,活多长都是不打紧的事。
尤其是活得愈久,看熟悉的人老而亡,看熟悉的人面目全非?
伊珏一直退回到洞穴入口处,找了个未清理干净的土堆藏身在后,边等着长平来人边同白玉山闲谈:
“人是个很嬗变的东西,我也是。但我可能永远是个野兽成妖的根脚,天性凉薄。”
所以他只做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不肯受人辖制,哪怕那些人是赵子虚的父母亲人。
他说起从前的事,说起狼妖和他的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