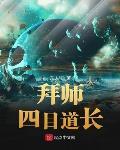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怎么还不亡国 > 第118章(第2页)
第118章(第2页)
安国的求援信发出去一圈,最后真的来的只有那几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而且还都只是表面功夫,精锐军队是没有派出了半个,全都是不知道搁哪儿抓来的兵卒,瘦小干巴的像猴子,上战场后连当先锋军的资格都没有,估计跑都跑不起来。
这让安王十分愤怒,觉得自己被耍了。
要不是现在在打景昌,安王都想转头去打那几个诸侯国了,这简直就是耻辱!
安王心里将那些诸侯王恨上了,如果他真的能躲过景昌这次的冲锋,或许沈知微就能看见狗咬狗一嘴毛的场景,但这只是如果,沈知微并不想让这种如果发生。
安国的领土被一寸寸啃下,比起北国,安国甚至更好打一点儿,因为安国国内并无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可守,唯一的天险就是一条横亘南北,贯穿安国的大河——安河。
像是这样宽的河,在其他诸侯国看来,渡河的方法实在是太少了,尤其是进入夏季后,安国这条河常常会水位上涨,水流很湍急,想要以船渡河也很难。
每年到了夏季雨水最丰沛的那个月,安国境内这条河就无法通过,好在这条河有的河段比较窄,有大桥能够通过,不然这一个月就得彻底隔开两端。
现在为了能够有效阻挠景昌的兵,安国将桥给拆了。
原本好不容易建成的大桥,说砸就砸断了,以后想要修上,不知还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但之后的损耗比起被景昌直接灭国的威胁,要小的多。
安王觉得安国能撑得住,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毁了那座桥,借助接下来要到来的涨水期,人造天险,阻挠景昌大军南下。
他想得挺好,这个办法也确实很不错,一旦战争再拖上一个月,指不定会出现什么变故,而且景昌是远征,粮草每日损耗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景昌不一定耗得起。
可惜这个办法出现的太晚了。
要是之前造船厂没有造出巨大的船只,或是船只数量稀少的时候,这个办法还有用,现在造船厂过不了一段时间就能造出一艘大船,商司需要的船只有限,现在都想着要不要往外探索,搜寻新的海上航路了。
如果水军能消耗一些船,那真是太好了。
于是,造船厂开始建造分厂,军队的后勤部队直接开始运送船只的半成品材料前往前线,原本真的要耗上一个月,现在不过半月余,水军就能下水了。
已经形成规模的大国在基建上的能力就是这么恐怖,哪怕是在古代,初具大一统国家气魄的景昌,也拥有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这期间,安国一直没有停下过小动作,他们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不管景昌想要干什么,他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
只是无奈实力有限,阻止的很困难,努力半天,结果一看,压根没有拖延几天。
也是在这个时候,安王终于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景昌的强大,已经凌驾于众诸侯国之上了。
如果沈知微是一个暴戾的君主,如果她治下的子民活的生不如死,那么诸侯国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她的可能,可她不光不暴戾,她还是一个堪称英明的君主。
在她治下,子民们安居乐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臣工也是一心为国,经过沈知微几次梳理后,一个作妖的都没有了,北王时期还能挑拨一二,到了安王时期,安王就是捧着一大堆金银珠宝,也买不通一个高级官员。
高级官员又不是傻子,反腐和叛国罪里那些落马的同僚是什么下场,高级官员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金银珠宝确实令人心动,可心动也得有命才能花。
安国如果能在景昌的大军下多坚持一阵子,或是能打得有来有回,那些高级官员也不是不能两头下注,为以后铺路,关键是安国压根没法反抗景昌,被景昌全程压着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眼见安国这艘大船就要沉了,还跟安王搅和到一起,那是纯粹的傻,高级官员里没有一个是傻子。
所以,安王不管如何努力,也没法复刻当时北王的行动,给景昌制造一些混乱了。
他想传播点儿谣言都做不到,景昌的口舌被报纸控制,妫央这个玩舆论战的也坐镇景昌,谣言刚传出去,还没传开就被扼杀了,要是不跑快点儿,散播谣言的安国探子就跟着一起死了。
安王不是没有努力过,也不是没有挣扎过,不是安国弱小,实际上现在的安国比之前的北国还要强一点儿,底蕴也更深厚,无奈现在的景昌,全面开始加速发展,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整体国力,都已经跃升到了上一层。
说句不好听的,景昌打诸侯国,那不叫打仗,叫降维打击。
钢铁铸成的刀剑与盔甲,更加精细的攻城军械,马有了马蹄铁,骑兵拥有了马镫,安国在弯刀和铁骑之下,脆弱的像是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