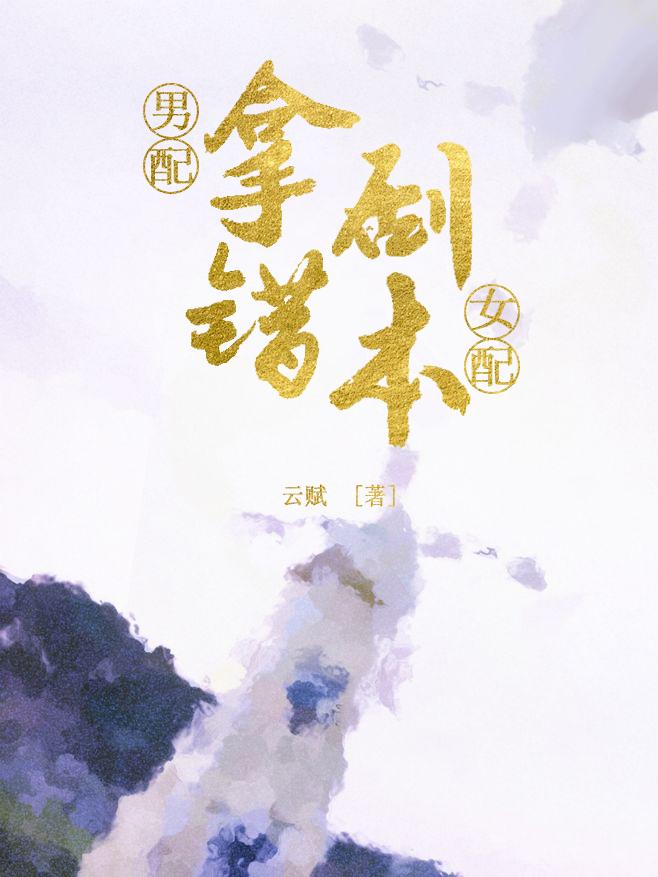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书剑定风波 > 100110(第15页)
100110(第15页)
只不过,世事总难完美。
卢臻刚好看见钟少韫自院子中穿行而过,怀里还抱着一些文书。
其实论起才能来,钟少韫一点也不差,很多事情上手很快,近些日子的大小平叛,就由钟少韫在中间沟通上下。这人很细腻,办事不会出错,也让卢臻很放心。
可是,为什么偏偏和卢彦则……
卢臻心里,让卢彦则按部就班的想法可以说是从未压下去,于是在钟少韫上前对他行礼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懒得施舍给钟少韫好脸色,希望以此来让钟少韫退缩。
同时,卢臻来到前厅招待崔善渊,“崔公,好久不见啊,哎,我没去你家反倒是让你百忙之中抽身,实在是我不对!”
崔善渊吩咐奴仆送礼,“那哪儿能呢?卢公现今是朝堂说一不二的人物,我怎么能让卢公亲自来呢!”说罢,整整齐齐的礼盒就堆满了灯火通明的前堂。
二人入座,奴仆斟茶,崔善渊先是叙温凉,又聊了点儿关于养生的话题,诸如黑发变白、皱纹变少这种道术,紧接着,就图穷匕见了,“哎,这人一到年纪就开始操心小儿辈的婚事,不知卢帅还未成家,是心里有意中人了么?”
卢臻很心动,崔氏是高门,更是幸存下来的高门,若是和卢彦则成婚,背后肯定能有不少襄助的地方,“哎,我这儿子,哪儿都好,就是犟。”
“这是有了?”崔善渊何等善于察言观色,“年轻人嘛,我这年纪也这样。”
“是啊,我还打算劝劝他,有些人玩玩就好,不能拿来做正室,娶妻娶贤,贤贤易色,崔公您说是不是?”
崔善渊点了点头,意识到这是卢臻在暗示,暗示婚事有说下去的可能,“是啊,卢将军一表人才,纵然一时想不开,到底还是能想明白什么最重要!”
二人聊了会儿就散了,卢臻走过前堂,对着芭蕉树说,“你听完了没?”
钟少韫隐匿在树影的黑暗中,并不多言语。
“我再最后劝你。钟少韫,彦则为了你,和我对抗,和很多人对抗,我并不喜欢他如此。你能帮他什么?你什么都帮不了。他年少气盛,狂妄,以为自己有权力就能事事如意,我告诉你,这是痴人说梦!世族互相拉拢,强强联合才是常态,而你,要么成为豢养的娈宠,要么就离开,只有这两个选择。”卢臻越说越气,好像一看到钟少韫原本的好心情就荡然无存。
因为他的一切来源于卢彦则,而钟少韫毁了卢彦则。
“你再好好想想,我没有耐心。”卢臻拂袖,“而你要是再死皮赖脸留下来,别怪我无情。”
眼看卢臻离去的背影,钟少韫难得地哭了出来,泪水流过脸颊和那颗痣,落在衣襟前。他这辈子不是没有争取过什么,从渭南一曲相逢,数次主动寻觅卢彦则,以及不顾一切地敲登闻鼓,宴会上弹琵琶,钟少韫都抱了目的。
看一眼,看一眼就好。
他总觉得自己和卢彦则距离很近,却不能忽略他们中间永远无法越过的深壑。
他争取过,命都不要。
现在看来,有些时候,尽管你能豁出性命,但性命在旁人看来可能和草芥没什么区别。
但他赶紧把泪水擦掉,因为卢彦则快回来了,劳累了一天,肯定没时间安慰他。
钟少韫迅速站起,回屋子里歇息了。
他和衣而卧,小憩了会儿,就听到有人敲门,卢彦则的声音略微带着疲惫,“阿韫,你怎么来这里睡了?是主卧房睡得不舒服?”
钟少韫刚想说话,发觉自己带了哭腔,一旁的枕头也被泪水打湿,于是赶忙把枕头翻了个面,用袖口擦了擦泪,站起身为卢彦则开门,“你来啦?”
“我没看见你,不大放心,听说你在这儿,就过来了。”卢彦则熟练地解开甲胄和披风,放到一旁架子上。这间房比较小,又在后院的角落里,其实卢彦则并不喜欢,他更愿意钟少韫去主卧房和他一起睡,“这么小,睡得惯?”
“嗯。”钟少韫点头,“小的话,一点炭火就能取暖,还不会有穿堂风,我睡习惯了。”
卢彦则忙了一天,终于能放松下来,偷点儿钟少韫攒够的暖,歪七扭八躺在钟少韫刚躺过的地方,革靴在床沿晃来晃去。见钟少韫背对自己,肩膀耸动,他不明就里,“阿韫,过来呀,你怎么了?”
“我没事。”钟少韫吸了吸鼻涕,“可能感染风寒了。”
“你眼睛有点肿。”卢彦则一把将其拉过来,钟少韫坐在他身侧,又是不看他的脸,“转过来,看着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没……”钟少韫枕着他的臂膀躺下,“你累了,该歇息了。”
“明天我就去问陈宣邈。估计有人给你穿小鞋,看你脾气好会来事儿就把你当牲口使唤。你不能憋着知道么?让人觉得你好欺负,他们就会一直欺负你,军营里,朝堂上,都是这种人。”卢彦则轻轻拍着钟少韫的头,“有谁对你不好,也要让我知道。”
钟少韫轻轻嗯了声。
“那今晚……”
卢彦则不知道该怎么提起这个话题,从那日的荒唐过后,他就不大敢提。可是总不能每次都自己解决吧?尤其是戳破窗户纸后,就难以抑制对钟少韫的情,握手或者接吻已经不够了。
尤其是四下黑暗,卢彦则又不是木头,钟少韫紧紧依偎在他身侧,如此刺激之下,他呼吸紊乱,先是在钟少韫的额头那里轻轻吻了下。
钟少韫并没有卢彦则想象中的畏惧或是抵触,反倒是迎了上来,白衣盖在卢彦则的绯袍上,眼睛里潋滟着泪水,“彦则,我很高兴……”
“什么?”卢彦则摸不着头脑,紧紧抱着钟少韫的腰,“我也很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