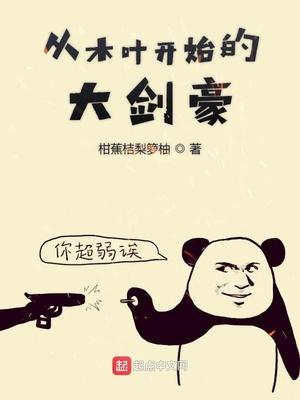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阿努特纳斯 > 110120(第2页)
110120(第2页)
当那颗彩虹的寸头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时,周遭一切白与黑的肃穆都在苛责这一幕的大逆不道。
所有人都理解她为什么会被揪出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道义和秩序的那杆秤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心里。
排队的女人们开始低声议论着些什么,好像她们是第一天看见寸头是这幅样子似的,陈立新涨红了脸想冲过去,却被两个眼疾手快的执行官按住了肩膀。
寸头在被拖走前最后看了她一眼,那眼神让她心神不宁。
卡车的后门关闭后,视野中的一切就陷入了黑暗之中。
陈立新和车厢内的十几个女人彼此挤靠着,度过了漫长的每一分每一秒。
傍晚,卡车停下来时,陈立新的袍子已经被她扣烂了一小片。
女人们排着队走下卡车,又挨个钻进一个个白色的小帐篷。
如同奔赴刑场的犯人般,陈立新始终低着头,满脑都是对寸头生死存亡的担忧。
每个帐篷平均分配两个人,陈立新钻进帐篷后,独自闷闷不乐地躺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个临时室友似乎有些眼熟。
怯生生的女孩整理好枕头后,转过身来看着她在地铺上的背影。
陈立新深呼吸一口气,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她坐起身来,朝女孩礼貌地伸出手。
“你好,我叫陈立新。”
“你那天提醒过我有人找我,我还没说谢谢呢。”
然而,面对陈立新的热情,女孩却仿佛被什么东西烫着一般。
她飞快地移开眼神,低着头摇了摇头,自顾自地将身体埋进了被子里。
“……那晚安啦。”
陈立新在心里叹了口气。
直到深夜,她才听见帐篷拉链被拉开的声音。
她猛地坐起身,视线越过早已睡下的室友,看向外面的人——她还活着!
寸头踉跄着爬进来,右脸肿得老高,嘴角还有干涸的血迹。
陈立新心疼地看着寸头的脸,用口型轻轻地问道:“她们让你干什么了?”
寸头摇了摇头,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一旁。
陈立新顺着看过去,室友正睡得香。
寸头凑到她耳边,低声道:“我被那个女的拉到最后面的卡车,被几个执行官打了一顿,然后……”
“我看见了那个带走我们的覆面女。”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陈立新心中闪过一丝希望的火光。
虽然那天,那个覆面女否认了认识自己,但是万一当时是特殊情况呢?
毕竟那么多同伴面前,说不定,她也有不能说出口的苦衷。
突然,寸头苦笑着摇了摇头。
“只是可惜,被打了一顿,我还是一个女的执行官也没看到。”
她话音刚落,就感受到怀中扑来什么温暖的东西。
黑暗中,陈立新轻轻地抱住了寸头,将对方的头拢靠在自己肩头。
冥冥之中,她隐约听见寸头压抑的啜泣声。
她只能握住寸头的手,低声说道:“他们要新的人口,至少说明她还能活着。”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她突然再次想到奕川和大学城里的女同学们,胃部不禁一阵绞痛。
接下来的一周,像一场模糊的噩梦。
每天黎明前被哨声惊醒,挤上密闭的卡车,一群人在不知名的黑暗和沉闷里度过五六个小时,傍晚再像货物一样被赶入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