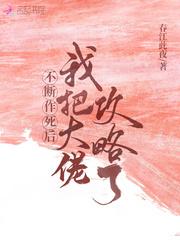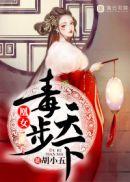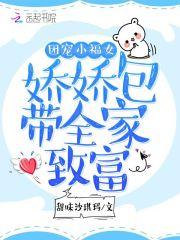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公主永嘉 > 7080(第10页)
7080(第10页)
还好令仪除了一开始问了一句,并未逼她,甚至不再看她,恍若她从未开口一般。
秦茵荣想起她的新朋友,想起夫子教过的道理,到底还是再度开口:“我有一个表哥,嘴上没个把门儿的,最为狂妄。昨日他见到我,得意洋洋地与我说,小姨昨日不在府中是为了去见父王,还说以后”她有些难以启齿地道:“再过不久我便该叫小姨王妃了我怕她们有什么算计,想着你若知道,能提防一二。”
一切反常果然都有缘由。
令仪默了片刻,道:“不必提防。”
秦茵荣问:“你就这般自信?”
令仪微微一笑:“她应该已经得手了。”
秦茵荣恍如被人打了一闷棍:“那”
令仪嘱咐她道:“你既然来告诉我,想必还是满意我这个母妃的。天要下雨,男人要变心,谁也管不了。可有些窗户纸,不戳破便不漏风,戳破了,便什么也藏不住了。所以这件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谁也不要告诉,你可能做到?”
这是将她看做了大人,秦茵荣郑重点头,忽然觉得不对,“你不伤心吗?”
她虽然年纪小,也听过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
更知道舅舅有新女人的时候,舅妈虽然不敢言语,可是表姐说舅妈私底下哭了好几夜。
可为什么父王变心,这个继母这般冷静?
令仪怔了下,露出一个难过的表情来,“我自然是伤心的,只是伤心也无用,你若为我好,便记住我刚刚说的话,此事谁也不要告诉,万不能让人知晓我已知道。”
明明刚刚继母交代自己时,她还有些骄傲,觉得自己终于变成了大人,可是这一刻,秦茵荣又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看不懂。
尤其是散学后,秦茵荣见到过来接王妃的父王。
王妃依旧笑容满面,被父王扶上马车的时候,秦茵荣又觉得自己还是太小了……
转眼便要到年底,皇上着令端王代他去冀州祭祖。
秦老将军当日遗愿,身埋冀州,死也要守望边关,因此新帝登基后并未迁移其棺木,每到年关需要人回去祭祖。
往年新朝初立,江山未稳,皇上不可擅离京城,都是由冀州族人代为祭拜。如今新朝已稳,这是初次由新帝祭祖,他派去的竟不是太子,而是端王,其间怎不耐人寻味?
秦烈又想带令仪一起走,令仪却不愿,冀州苦寒,他这一行匆匆,来回不到一个月,路上势必要快马疾驰,且万一他回不来,过年时总要有人去宫中,若她这个端王妃也不在,实在太过显眼。
况且秦烁去年刚与大理寺卿家的二小姐订了亲,过年势必要走动,府中岂可无人?
秦烈思及此,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临走前一夜,早早地把她拐上。床。
令仪揪着他的衣领喘气,“你最近为何总不脱衣衫?”
秦烈低笑:“不脱衣衫,也不妨碍我将公主伺候的妥妥帖帖。”
令仪翌日醒来时,他已启程,之后每隔三日便收到他的信,也没什么别的话讲,只说他今日到何处,吃了什么,吃到好吃的也会差人随信送过来。这种报平安的信,没什么回复的必要,不想再来信时,他在信中问她府中有何事。
令仪便让秦烁他们三人各自给他写了封信,自己也回了一封,写他送的哪些吃食她很喜欢,回来时可多买些,又写待过几日小年后,学堂休学,她便要带着孩子们去庄子里,让他不要再写信来。
这次的信来的格外快,他说自己写信无非是因为想她,可她的回信字数那般少,显然并不思念自己。
字里行间竟带着几分幽怨,令仪将信收起,只当自己没收到,带着孩子去了庄子。
这次到庄子上,焕儿又大了一岁,不便与她一起住,也单独住了一个院子。
秦烈不在,他们愈发肆意,终日骑马射箭,嬉戏玩闹。只是这次秦茵荣显然认真起来,纵然再度比试落后,也没耍脾气,反而一箭一箭地练,一日不曾停歇。
令仪没去与他们胡闹,往日里过来,身边总有秦烈,今年难得一个人,她独自骑马上山。
京郊并无大山,这片山头都归端王府,并无危险可言,是以只有两名侍卫不远不近地跟着。
她终于到了山顶,之前下了场雪,山下已然融化,只山顶依旧皑皑,呼吸都是白气,她眺目远望,心底一片澄澈清明。
直到感到一人接近,她猛然回头,只见一人穿着侍卫服饰,已来到她身后,身材高大,浓眉压目,依旧气势十足。
她惊呼出声:“你怎么会在这里?!”
宋平寇近乎贪婪地看着她,“我来带你走,同麟儿一起离开中原!”
一提到麟儿,她便泪盈于睫,“他可还好?你救出了他?”
在保下麟儿性命后,她终于让秦烈答应她,由三娘照看麟儿,且每过半年,她要见一见三娘。借此保证麟儿的安全,三娘宁死也不会负她,必然会善待麟儿。可即使麟儿再安全,她也再也见不得他一面。
宋平寇伸手抚去她的泪水,柔声道:“我去看过他,只不敢打草惊蛇,想等救了你,再去找他。到时我带你们去海岛,那里终年没有雪,岛上长着高高的树,树上结着未曾见过的果实,里面有黄色果肉,闻着难闻吃着却美味。还有一种果实,外面坚硬,打开后里面有白色的汁液和果肉,清甜可口,你一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