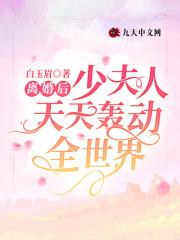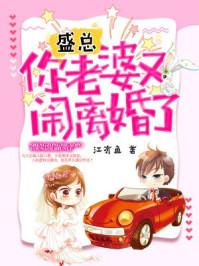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不系之舟(1v3) > 番外9被世界遗弃的角落齐线(第4页)
番外9被世界遗弃的角落齐线(第4页)
她几乎要呻吟出声,身体深处泛起一阵空虚又饱胀的酸软,那是极致欢愉过后留下的生理记忆。
但下一刻,更庞大、更沉重的现实如同冰水,兜头浇下。
视野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不是纽约公寓开阔的天花板,而是北京家中卧室熟悉的、带着岁月沉淀感的木质吊顶。空气里没有哈德逊河的水汽,只有淡淡的、属于老房子特有的檀香和书卷气。窗外也没有不夜城的喧嚣,只有清晨微熹的天光,和偶尔掠过的、孤单的鸟鸣。
安静。一种令人心慌的安静。
她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冰冷的。没有方欣温软的身体,没有她入睡后均匀的呼吸声。
方欣。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捅开了记忆的锁,放出里面盘踞的、名为“失去”的巨兽。
八年了,在新加坡那家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疗养院里,她曾经亲手合上那双曾经盈满甜蜜与风情的眼睛。骨灰带回了香港。她记得那天的天色是灰蒙蒙的,海风带着咸腥气,吹得她眼眶干涩,流不出一滴泪。
而Joyce……齐雁声……
霍一缓缓坐起身,骨骼发出轻微的、不再年轻的声响。她抬手揉了揉眉心,试图驱散那个过于真实的梦境带来的晕眩感。
她和Joyce从未一起去过纽约。
在纠缠最深那几年,她们的足迹遍布东京代官山,伦敦西区,甚至冰岛的极光下,但唯独没有纽约。那个位于世界之巅的意象,更像是她少年时期某个不切实际的憧憬残余——一个完全脱离原有轨道、只有她和“理想爱人”的、真空般的乌托邦。
十七岁的她曾经幻想过,和以后的爱人蜗居在纽约的顶层公寓,她渴望在异国他乡的高楼俯瞰风景,在烈风中接吻,长久拥抱,然后在铺天盖地的雨里,在落地窗边做爱,隔绝时间,隔绝喧扰,只有她们,城市,车流,人海,都成为泛泛的背景。
是梦。只是一个因为积压了太多无法排遣的记忆而衍生出的、无比逼真的梦。
可为什么是Joyce?为什么在方欣逝去,妈妈老迈的现在,梦境会如此清晰地召回Joyce的身影,召回那些激烈到近乎疼痛的亲密?
她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在微凉的地板上,走向客厅。步履间,梦里的触感似乎还在隐隐作祟,尤其是腿心深处,那种被填充、被撞击的幻觉久久不散,带着一种荒谬的、生理性的湿润感。她厌恶又迷恋这种身体对虚幻的忠实反应。
给自己倒了杯冷水,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稍微压制了胸腔里那股莫名的燥热。她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北京初夏清晨的风,带着植物叶片的气息,温和而克制,与梦中那种仿佛要摧毁一切的烈风截然不同。
“风太大,小心冻亲。”——梦里Joyce的叮嘱,带着柔软的腔调,仿佛还在耳边。
霍一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都是假的。
真实的,是方欣已经冰冷的墓碑,是妈妈日渐增多的白发和偶尔流露的、需要人陪伴的眼神,是……是齐雁声也已经归于尘土的现实。
那个在舞台上挥斥方遒、在生活中八面玲珑、在私底下对她展现出惊人开放与纵容的Joyce,那个让她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矛盾综合体,也早已不在了。
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细密而真切的绞痛。她按住胸口,眉头紧锁。
打开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冷光在未完全亮起的房间里,她熟练地打开浏览器,手指在触控板上无意识地滑动了几下,最终,却像被什么无形之力牵引,点开了视频网站。
搜索框里,她几乎不用输入完整的关键词,联想列表就跳出了“齐霍”、“玄都手札”、“齐雁声
霍一”等标签。
她点了进去。
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剪辑视频。数量之多,生命力之顽强,远超她的想象。
她以为自己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以为随着齐雁声的离世,那些陈年旧事会被迅速遗忘。然而并没有。
也许是因为《玄都手札》那部剧在多年后,因其独特的悲剧内核和女性视角,被重新评估为某种“神作”;也许是因为她和齐雁声之间那二十多岁的年龄差,在当下“姐狗”、“姨狗”文化盛行的语境下,反而成了萌点;也许,就像那个梦一样,人们总是热衷于在蛛丝马迹中,寻找那些超越了世俗规范、幽微而深刻的情感联结——就像评论区有人提到的“袁立和李红”,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足以让人津津乐道多年的氛围感。
“悼念我嗑的第一对BE上古大神CP……”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
“正主一个长居北京,香山红叶,深居简出,一个埋骨香港,地久天长。生死之间,一南一北,何其遥远漫长。”
“面如微云素月,何其隽永的印记,点一首指纹给我们悲情齐霍”
“可是她们真的好真……”
霍一的目光扫过这些评论,心情复杂得像打翻了的调色盘。有荒谬,有讽刺,有一丝被窥探的不适,但更深层的,是一种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