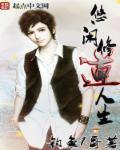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从岭南孤女,到开国帝王 > 议定封赏(第1页)
议定封赏(第1页)
属于姜渺的殿试已然结束,但对含元殿内的公卿大臣们来说才刚刚开始。
皇帝俯视群臣,缓缓开口:“诸卿以为,今日殿试,何人可为魁首?”
这明显就是在带着答案问问题,台下站着的可都是人精,有谁看不出来皇帝心中早已属意姜渺?
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
最后还是吏部尚书谢洵站了出来,他躬身道:“陛下,以今日之见,论学识、诗才、心性,姜渺都远超同侪,理当为殿试头名。”
皇帝点头笑道:“既是头名,依照本朝先例,便该点她为状元,但不知该封她个什么官当?”
“不可!”
出言者仍是吏部尚书谢洵。
“嗯?”
皇帝颇为不悦地看向谢洵:“你方才既说她当为殿试头名,又如何能不封官?”
谢洵神色不变,语气坚定道:“臣言姜渺此人当为状元,是因其才学出众,然陛下要授其官职,却大为不妥。”
“有何不妥?”皇帝声音转冷。
“姜渺身为女子,便是最大的不妥!自古以来,岂有女子位列朝班之理?牝鸡司晨、纲常紊乱,恐非社稷之福,还请陛下三思!”
谢洵说完这话,便一揖到地,大有皇帝若不同意便不起身的意思。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带头,其余官员们也都有样学样的反对起来。
“陛下虽有爱才之心,但那姜渺,年不过十一,纵然有些小聪明,但毕竟见识短浅,授以官职,于礼不合!于制不符!倘若处理政务稍有疏漏,岂不贻笑大方?”
“女子为官,除蛮夷外,我中原正朔,闻所未闻!若开此先例,必将使士林哗然,天下震动,届时我朝与北蛮又有何异?”
“《礼记》有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姜渺既熟读经书,必知其理。却从广州一路乘车马入京都,殿试当日浓妆艳抹、身着华服,招致他人侧目,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此投机取巧的无德之徒,陛下却要让她入朝为官,臣实恐阴乘阳位,乾坤倒悬啊!”
“……”
反对给姜渺授官的声音一浪比一浪高,几乎占据了文官队伍的十之八九,而剩下的一分也只是看皇帝神色不悦而暂时保持沉默罢了。纵使有如江佑一般对姜渺的诗才大加赞赏的官员,在面对这个原则性问题时,也都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
皇帝看着台下这些个群情激奋的臣子,脸色渐渐阴沉。他竟不知这些平日里为利益资源分配不均而相互倾轧的官员们,此刻竟然出奇的团结,将矛头一齐对准了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不过,他们反对的究竟是姜渺一人,还是自己设立的“童子科”,亦或者,二者皆有?
皇帝在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纵使已怒气填胸,却又不得不强行压下,冷声道:“朕开‘童子科’,就是要打破常规,于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拔非常之才!姜渺之才,今日殿上,诸卿皆是亲眼所见。若因其为女子而弃之不用,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朕食言而肥?耻笑朝廷无容人之量?”
面对皇帝的质问,谢洵不为所动,姿态虽还恭敬,声音却步步紧逼:“我朝向来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开科取士,不过是建兴年间逆臣所为,幸得先帝拨乱反正。陛下却……若陛下执意为姜渺授官,与我等同列,恐怕将使天下士子离心啊!孰轻孰重,还请陛下三思!”
这话说得极重,将皇帝和本朝定性的逆臣放在一块比较,就差没指着皇帝的鼻子骂你这个昏君了。
但谢洵不怕,他出身陈郡谢氏,有家族荫蔽。自己又身为尚书省下的吏部尚书,官员的考核、选拔之权都在他的手里,朝中依附者无数,就是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果然,谢洵语毕,一群官卑职小的官员们也都纷纷伏地恳求。
“还请陛下三思!”
“陛下!三思啊!”
“哈!哈!”皇帝拍案而起,手指众人怒极反笑:“三思三思!都叫朕三思!朕知道,你们都是忠臣!良臣!贤臣!朕今日若是不听你们劝谏,岂不成了是非不分、刚愎自用的无道昏君!”
“陛下息怒。”
“朕如何能不怒!”皇帝一振袍袖,还要再说,瞥见说话之人乃是尚书令王偲,声音顿时软了几分:“王公,你与他们也是一般所想吗?”
见王偲发话,方才还乱糟糟的朝堂瞬间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