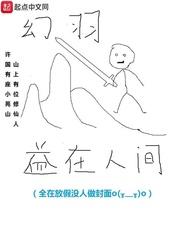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玛丽安娜的地狱七日 > 第10章 永别了武器(第2页)
第10章 永别了武器(第2页)
并不算深,那恶魔是想一点点把这物件整个塞进下体折磨自己,却没想到被还没怎么开始就被反杀。
那个畜生现在正瘫坐在墙角的铁架边“嗬嗬”地喘着粗气。
往外拔的时候,尽管她已经足够小心谨慎,但锋利的边缘还是在割伤少女体内娇嫩的肉壁,疼的她中途松手了几次。
不过和这几日受到的痛苦和屈辱来比,算不了什么。
“哈啊……”
翼饰离体还牵出些许泛红的银丝,玛丽安娜颤抖了一下,随即挣扎着撑起身子坐在桌上,拿衬衫前襟擦拭上面沾着的体液和血丝。
被冷汗浸透的衬衣上留下红印,这件浅蓝色的军装衬衣快被她的血染红了。
翼饰上花纹的缝隙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她只能作罢,把这用自己血液做勾线的装饰带回头上。
白皙精巧的双耳再次被这两片金属保护,熟悉的冰凉触感让她感到安心。
外面的雨声似乎变小了,也有可能是错觉。
刚刚被卢卡斯用犬链勒住脖颈造成的窒息感和头晕目眩还在影响着她,玛丽安娜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在动脉里奔腾的隆隆声。
她看向靠门侧的墙角,前几日被按在这里轮奸时,她依稀瞥见自己那身可怜的军装被堆在那里。
理智和自尊如同潮水般回归玛丽安娜的心里,她完成了复仇骂,她不再是任人羞辱的玩物。
女性的矜持与自爱让她想穿上衣物,然后走出战壕坦然迎接命运,尽管那套军装已经被撕扯脏污地无法入目。
那个角落空空如也。
“被扔了吗……”
玛丽安娜自言自语,这些恶魔就算是死,也要羞辱她最后一次吗?
她低下头,看到夹在双乳间和手腕上穿成串的铭牌,那些她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德国士兵,那个为了兄长复仇而殴打她的马塞尔……那个惨死的工兵,这些人的死状像画片一样在眼前闪过。
“……唉……”
他们都死了,她还活着,至少暂时是。某种沉重的情绪压在心头。
乳首上被别着的勋章像是在发烫,这是对她,也是对那位卫国英雄的羞辱。
她想取下来,可上面的创伤兴许是有些发炎,乳首涨得难受,玛丽安娜怎么努力都取不下来,只得放弃。
她现在虚弱得连自愈能力也失去了,也许能被一个十岁的孩童轻松击倒。
玛丽安娜从桌上下来,蹒跚着走向墙角,她想在旁边的杂物堆找找有没有什么蔽体物品。
地面很干燥,足底踩在沙土上让她觉得发痒。
“对不起……嗬……对不起……玛丽安娜……对不起”
卢卡斯有些变调,混杂着血沫翻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吓得玛丽安娜一惊,双腿站直立即转身看向他瘫坐的墙角。
万幸,那个恶魔还是濒死地蜷缩在铁架旁,看起来出气比进气多了。
灰色的石肤几乎覆盖了除腰间创口和面部以外的区域,肠子几乎从腹腔里全撒在外面,血液在身下汇聚成水潭
让玛丽安娜有些奇怪的是,那个手状的黑泥面具从他脸上消失了,露出德国人常见的褐色眼睛。
“你在跟我道歉?哈哈,之前那样折磨我时怎么没有想过停手?!虐杀那个英雄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心存善念?!”
玛丽安娜被这莫名奇妙的道歉气笑了,愤怒着质问这死到临头还在虚伪的魔鬼。
“我,我……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我不能控制我的……身体……对不起,玛丽安娜……”
卢卡斯双手握着剑刃,肺部喘得像个破风箱,他努力保持还算清醒的理智。
“你什么意思?你这个混蛋?你不会想告诉我你有多重人格这种老套的桥段吧。”
玛丽安娜脸色发冷,她突然发觉卢卡斯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熟悉的另一个声音。
“重塑之……手在开战前,就,就……污染了长官,污染了所有人……我……”
卢卡斯哭泣着断断续续说,脸色苍白得像是塑像,语速越来越慢随后昏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