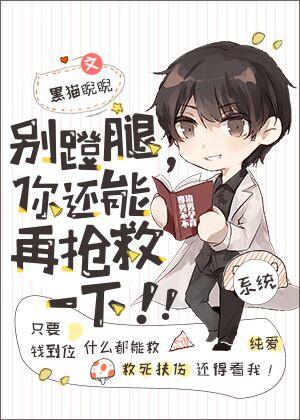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综英美]如何拒绝与前男友复合 > 第 16 章(第1页)
第 16 章(第1页)
看心理医生是每个特工和警察都不得不品尝的工作生活的一环。
克莱尔觉得没什么用,她只是七天去见一次心理医生,蹭咨询室的茶水。卡莉法坚持要她每周都到咨询室报道,哪怕克莱尔从来没向医生吐露埋在心底的任何秘密。
“对一个陌生人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行走一样。”克莱尔评价。
“所以,我算是你给自己挑的心理医生吗?”夜翼问,“每个你去见心理医生的晚上,你都会约我见面。”
克莱尔把喝空的啤酒罐捏瘪,懒洋洋地仰着脖子,“比较好听的说法是男朋友,比较难听的说法是男性朋友,你选哪一种都可以。”
“我不记得你有向我表过白。”
“是吗?我也不记得了。”克莱尔把一袋巧克力豆砸到夜翼身上,大方道,“等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找我,我愿意倾听你的烦恼。”
“得了吧,我不会给你嘲笑我的机会。”夜翼说,他没动桌上的啤酒,单手打开了一罐气泡水。
克莱尔扬眉,“你肯定对我有误解。”她把皱巴巴的啤酒罐收进脚边的垃圾袋里,方便等会儿带走。
游艇依旧卡在某一道流程里,克莱尔悲观地认为自己下次见到它会是三年以后。这让她的小港口变成了一个私密安静的空间。
她在栈道附近搭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堆满零食和酒水。她和夜翼每周在这儿碰一次面,像布鲁德海文的潮汐,每到一个特定的时间,便会回到特定的地点。
她们有时在傍晚碰面,燃烧的夕阳格外美丽,黄昏在身旁的海面上燃烧。
有时见面的时间拖延到晚上,克莱尔点亮栈道前的小灯,一点灯火吸引飞蛾不停朝灯上撞。
夜翼不来她也不恼火,夜翼赴约她就和他说说话。
她第一次向夜翼发出邀请时,夜翼错过了约定的时间,他迟到了三个小时。他知道克莱尔不会等他,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他在天明时分到达港口。
栈道延伸向海的尽头,一团模糊的影子坐着。克莱尔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靠海最近的位置,喝着啤酒等海上的日出。
那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她一定能看到一场壮丽的日出。夜翼远远地等待,直到恢弘的橘红色破开紫灰的海面,在翻涌的海的另一边升起,
云朵、船只与栈道尽头的克莱尔都被勾勒出一层浅浅的金光,然后,日出吞没了她们,夜翼悄无声息地离开。
他忽然明白了克莱尔为什么会坚持每周玩笑似的碰面。她和夜翼之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定位,他不敢问,她没有说。
事实原来是如此,布鲁德海文不能算是一个对外来者友善的城市。她、他、她们都需要一个不用袒露秘密、不用紧绷神经的空间。这是克莱尔没有在“迪克”面前表现过的,夜翼心里把这描述为“休息室”。
于是他默认了“休息室”的规矩,每周都在港口和克莱尔漫无边际地闲聊。他们各说各的,不指望另一个人能给自己完美的解决方案,也知道对方不会无穷无尽地探究自己的隐私。
不插手,是克莱尔与夜翼微妙的默契。
“你今天点了豪华装的寿司外卖,”夜翼灵活地使用筷子,夹走一片三文鱼,“看来你这周有值得庆祝的事情。”
“是的,我重新开始接案子了。我的上司卡莉法从BPD手里给我抢了点活儿。”克莱尔挑眉,“它的另一重含义是,我再也不用去见我的心理医生了,真棒。”
夜翼的另一重身份很了解海文警局的种种毛病,他若有所思,“BPD都嫌弃的案子,很棘手吧?”
“不,警局咬得很死,不愿把案子分给我们。”她没有多说,而是用筷子别住夜翼的筷子,和他争夺最后一块寿司。
两双筷子在半空中打架,噼噼啪啪。夜翼用空出来的那只手偷走了鳗鱼寿司,得意地冲克莱尔笑。
克莱尔意味不明地勾起嘴角,当夜翼发现鳗鱼寿司是一个陷阱时为时已晚,辛辣呛鼻的芥末味直冲天灵盖。他痛苦地扭曲脸色,半天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