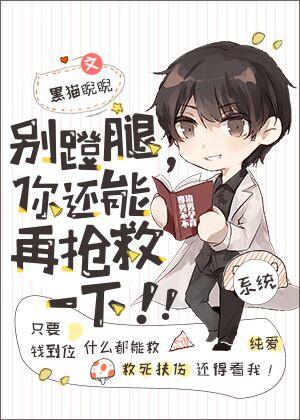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替身反攻略指南 > 7080(第4页)
7080(第4页)
见时星洄不解地抬头,温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对方的双腿,“不给我留个座位吗?”
剧本里并没有这一段,是温酌发现她的心不在焉后刻意加进去的。
时星洄倏然回神,将手从膝盖上移开,随后,馥郁馨香袭来,温酌跨坐在了她的腿上,惊艳万分的眉眼认真地注视而来,“奴家还从未与人欢好过,云姑娘可要温柔一些。”
左胸口的跳动失去了原有的节奏,就好像彰显着正在失控的自己,时星洄抿紧了唇,垂眸躲避那格外炽热的视线,“柳姑娘,我不是来……”
后颈被轻轻地捏了捏,温酌就像一只刚刚化形的狐狸,鼻尖一寸寸嗅过时星洄的锁骨、脖颈,乃至耳后。
温热的吐息喷洒在肌肤上如同点燃干柴的火源,被发丝遮掩了半日的薄红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温酌发现了时星洄也并非无动于衷后,墨色的瞳眸渲染上几分苦尽甘来的笑意。
不过,剧情还在继续。
只见温酌眸光一凛,微微拉开了一些距离,诧异问:“你身为乾元,怎么会没有味道?”
像是找到了什么理由,时星洄放轻动作推开了温酌,低声道:“我、我不行,柳姑娘,在下来此真的是为了别的要事。”
温酌眼中的情绪几经变幻,最后全都化作苦涩,她勾唇一笑,收起了那副娇媚做派,眼神反而折射出清泠泠的冷,“可是明日,若我身上并没有被标记的痕迹,这入幕之宾,怕是就不止云姑娘一人了。”
也不知明日,可还有这样看起来干净又温柔的人出现。
时星洄浅浅蹙眉,欲言又止,可是看着温酌自怨自艾的模样,最终还是道:“柳姑娘,我知你处境不易,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温酌歪着脑袋看来,流光溢彩的眸间漾着极淡的兴趣,更多的是如死水一般的漠然,“说来听听?”
“黑市上有售卖伪装信香的香水,一般是提供给天阉之人助兴的,而这个,我有,或许可以帮助柳姑娘逃过检查。”
兴趣肉眼可见地浓了一些,温酌眼波流转,终于专注且郑重地落在了时星洄的身上,再不带一丝冷漠的玩味,“黑市常人难以进入,看来云姑娘比我想象中要更加高深莫测。”
“柳姑娘只需要告诉我答案就可以了。”
“当然,我同你做这个交易,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想要你,帮我搞定县令公子。”
温酌勾唇浅笑,手在脖颈间比划了一下,“杀了他?”
时星洄被哽住了,赶忙摆手,“不至于不至于,我只是想要取得营业资格而已,他说若我能让你与他见上一面,便不再卡我。”
“原来如此。”
温酌撩开了披散在肩头的乌发,露出纤长细白的颈,随后妖冶万分地抬眸看来,“演戏演到底,送佛送到西,云姑娘既然要帮我,至少要留下一些痕迹吧。”
闻言,时星洄只好慢吞吞地走了过去,目光落在那冷玉一般白皙细嫩的肌肤上,她知道的,温酌不怎么爱晒太阳,所以每一处都生得如同冬日落下的新雪,白得好似反光。
而且几乎每一处,她都细致地抚摸过、轻吻过,所以更能知道温酌身上每一颗隐秘的痣。
喉咙不自觉地上下滚动,时星洄缓慢低头,唇瓣寻着温酌的后颈,仿佛真的即将在那里落下一个轻柔的吻,又或者说,一个无人可知的标记。
温酌努力抑制住来自神经深处的颤抖,害怕自己哪怕一丝的举动都会惊醒此刻的时星洄。
剧本里的云边,是没有吻上去的。
可是,温酌等待这一刻,却是流尽了眼泪,受尽了苦楚,如同正在朝圣的少女即将得到神明的青睐,她攥紧了拳,眼眶都微微泛红。
带着热度的呼吸停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既没有彻底离开那样令人难受痛苦,又没有再拉近,令人心痒难耐。
时星洄被理智束缚住了动作,第一个反应却不是起身,而是皱眉,她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明明想起了剧本的走向,但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一片雪白和淡淡凸起的骨骼,还是想……咬下去。
是报复吗?
劫后余生一般急忙离开仿佛能蛊惑人心的娇艳美色,时星洄压抑着喘息,强撑着理智念出了剧本里的台词,“抱歉,柳姑娘,在下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不能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
失落,极致的失落。
就好似心脏突然空了一大块,在八月中的夏日被灌入了极寒之地冷冽刺骨的风,像锋利的刀刃一下下划过脆弱的血肉,温酌咬紧了唇,被突如其来的哽咽堵住了发声的能力。
见她许久都没有回应,时星洄探究看去,却对上了一双湿漉漉的、盛满了破碎委屈的眸子。
不,这不是柳瓷枝该有的表情,这是独属于温酌本人的,极度脆弱又极度倔强,极度渴望又极度隐忍,最为矛盾的神情。
左胸口的跃动活泛起来,时星洄转身躲开对视,拿起自己放在吧台的水再度喝了起来,“那个,今天就对到这里吧,也差不多了,最后那一部分明天在剧组看看就行。”
“嗯。”
温酌的嗓音闷闷的,她抬手轻轻抚过仿佛还残存着温热气息的后颈,低声道:“对不起,我有点不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