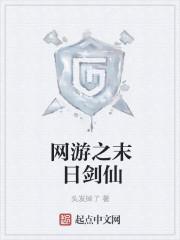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水浒]掀翻大宋 > 240250(第4页)
240250(第4页)
此时他的任期也快满五年,这一走还不知能不能再回归,便嘱咐了明府尹和两浙转运使吴祥许多事宜,着重强调让转运使大人联络广德军王昭德,派兵到润州,沿岸守好润州城。
明翰海大惊失色,“那金军竟然这么厉害,能打到江南来不成!”
潘邓说道:“事有万一,不可掉以轻心。”
*
汴京城,皇宫之内。
新皇即位之后改了年号,叫朝中大臣看到了些希望,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新年,群臣们都盼望着这个国号能够给大宋朝带来好运,能让国家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然而从前低迷的氛围虽不见了,此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大家都三缄其口,轻易不说话了。
本来太上皇在位之时,朝中人多数都是主战派,支持皇帝联金伐辽,事实上这一决定也着实取得了很多成就,太上横扫北方,夺回燕云十六州,杀伐果断,功勋卓著,其能自太祖以后未曾有也!群臣也一并跟着光荣起来,该升官的升官,该封赏的封赏,皇帝一个都没落。没见那童贯一介宦官之流还被封了异姓王吗?这是多大的殊荣!
然而如今金军南下,眼看着就要到汴京城,太上退位,连着和他的宠臣们一起失势,这似乎又说明主战派的决策并不正确。
那如今又该怎么办?应该主和吗?是战还是和,这个问题连太上皇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以至于直接把烂摊子丢给自己的太子了。
可这样的大事对于新皇来说也着实太过难以抉择,他以前参与政事,从来就只是就着不好的地方劝谏一番,没做主过什么重大的决策;从前所学,也不过礼义仁孝,虽学过许多祖宗仁慈之法,也听过祖宗如何征战,可乍然面对国家风雨飘摇,也全然不知如何行事,内心一点章法也无。
如今刚一即位,就要主持直接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对重重的声音叫他尽快做决定,赵桓心中焦急,内心满是惶恐。他回想着自己的父皇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最终想出来了——父皇遇事难以抉择,通常都找太师商议。
可如今的太师是陈文昭,赵桓皱了皱眉头,从前若不是朝中奸臣作祟,叫他父皇联金伐辽,种下恶因,又岂会有如今的苦果?
他做太子之时就见不惯朝中奸臣做派,如今做了皇帝虽不能拿他们如何,却也不会再宠幸奸臣,赵桓左思右想,最终决议叫大臣一同商议。
皇帝叫众臣商量对策,这下众人也不好闭口不言了,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之下,赵桓发现此时朝中大臣多数竟然依旧主战。
不光是陈文昭、宴眘之流,就连曾经反对他父皇决策的宇文虚中,此时也坚决主张抵抗,并且提议皇帝再下诏令,急召各地军马前来京师勤王。
既然如此,赵桓便没有犹豫,召集西北军、东路军前来勤王,只是轮到江南军时犹豫片刻。
吴敏见状说道:“太上在位之时,已经发了几封急信送往江南,想来潘大人不日就会来到京师。”
赵桓听了这话舒了口气,如果说北宋军队还有哪支能够抵御西北,除去西北军,就只有江南军了。
赵桓于是暂时放下了心中的成见,在此危急时刻,反而有些盼望潘邓的到来,心想有能之人不必多加苛责,他只要能来汴京城救火,就是忠臣良将。若是大宋真能平安渡过此劫,自己日后也真做了皇帝,必不会薄待他。
*
前朝商讨对策,赵佶在自己的寝宫中也在琢磨着究竟什么时候逃跑,往哪儿逃。
杨戬和蔡攸、王黼等人根本没去前朝,而是围在太上皇身边,劝道:“陛下,你快走吧!”
赵佶也挨个劝道:“杨卿家、蔡卿家、王卿家,你们也走吧!”
杨戬几人根本就没想留在汴京,就等着太上皇说这句话呢,听了之后忙不迭的答应,“陛下,咱们一块走!”
赵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他和宠臣之间一向无可不言,问道:“几位卿家因何不留在汴京?”
杨戬说道:“现在一众朝臣都围在新皇身边,哪里有人再来看望陛下?臣等担忧陛下南下遇险,愿为陛下保驾护航!”
赵佶顿时内心感动,连连说好,准备带着他的宠臣们一同南下。
王黼和蔡攸对视一眼,他几人说是担忧陛下,实际上是保全自身,只因新皇即位没有三四天的功夫,朝臣便向着他们这些昔日太上皇身边的红人发难了。
太学生陈东直接上奏皇帝,要求处置奸臣,他把蔡京、童贯、王黼、杨戬、梁师成,李彦几人称为“六贼”,请求皇帝诛杀几人。
如今前朝也不知在嘀嘀咕咕商量些什么,几人内心惶恐,生怕过不了多长时间,新皇帝就要找他们清算了。毕竟金军南下,总要找人背锅,从前太子就看他们几个不顺眼,如今怎能轻易放过?
真是苍天无眼!从前谁能想到陛下鼎盛之年居然就要退位,新皇这么快就即位了!早知道他们就多拍太子马屁了,何必对太子诸多冷眼?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事无常也!
赵佶收拾了包袱想要走,然而朝臣却不会轻易让他离开,太师陈文昭劝道:“陛下何故欲弃城而逃?此乃危急存亡之秋,陛下身为一国之君,万万不可离去!新皇刚刚即位,根基未稳,若陛下此时弃城而去,士卒见了必会军心涣散,届时无人守护城池,百姓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果不堪设想!陛下,万望三思而后行!”
赵佶背上了道德枷锁,抱着行李包袱在寝宫多待了两日,十一月初五,北边突然传来奏报,黄河失守。
赵佶当夜二更天就从通津门水路出城,带着自己的宠臣后妃一路南逃。
*
“黄河怎么会失守?来的是西路军还是东路军?”
开封就在黄河以南不远,黄河失守,他们也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