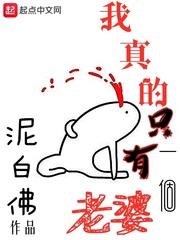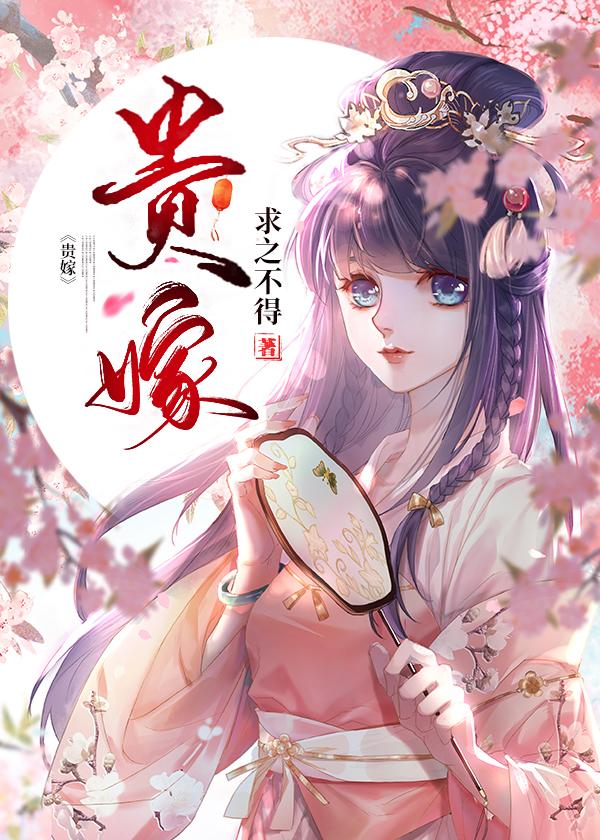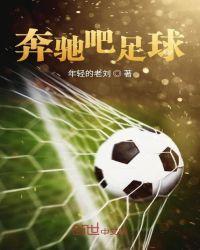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水浒]掀翻大宋 > 120130(第11页)
120130(第11页)
观战之处站了一排的指挥使,都监,还有两位府尹。
那穿着官服,背手站立在小山坡上,眺望远方,看着面嫩的,就是东平府潘府尹;那穿红袍披银披风,头戴官帽,脚蹬皂靴,白须利落,拿着一个单筒望远镜,双眼一睁一闭,目不转睛地探头往前瞧的,正是济州张太守。
张叔夜此次亲自前来东平府,为的就是采买兵器一事,恰好这几日总有演练,便来一观。
那府中通判王春、督监黄城明都劝他不要来,真是胡闹!他不亲自来能行吗?他要是不亲自来,能得到这“千里江山镜”吗?那王通判还要替他前来,他来的明白吗他!
张叔夜观看战局,熟练的转动镜筒,调节距离,眼看此处人马隐入山中,已然不见,又登登登大步走到东边,拿着望远镜看起了另一伙人。
山中两营队伍,已经开始各自占据有利地形,一刻钟前,蓝队已经发现红队分兵,决定加强高地防御,同时派遣游击部队沿山南线进行拦截。
此时红队已经遭遇蓝队,小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双方枪棒交加。
张太守转动镜筒,见混战之中,那蓝队队员用枪棒在红队身上点了好几处白粉,不由感叹,“唉呀……大势已去呀……”
被点了白粉的队员便是已被“杀死”,只能留在原地等待。
不止张太守一人叹息,那梁山之上也有目力好的,从山上向下看,忍不住拍栏杆,“眼看就要成了,怎么就让那蓝队的给截住了!”
旁边人叫他小声一点,那人声音放小,又继续说道:“此时若是没遇到蓝队,这事就成了!”
“这红队也是人太少,又没有高手。”
“选的路线也不好,要是我,定不走这条道!”
“就是就是。”
张叔夜摇摇头,红队分兵太过,太分散了,如今损失惨重,剩下的兵力已经没法和蓝队抗衡了。
“胜负已分……”
张叔夜把望远镜放下来,叫它自在脖子上挂着,揉了揉胳膊,刚要歇歇眼睛,却看周围除了同样有望远镜,负责记录战况的一个虞侯正奋笔疾书之外,空无一人。
“嗯?”
他猛的往那边一瞧,见一群东平府的指挥使正围着几个奇形怪状的架子。
潘府尹也好似正在检查。
有几个人现场做了示范,吴指挥使与王指挥使一前一后把那担架打开,把那平躺着的虞侯抬到担架上,再调整方向,半蹲下去握住两边铁管,抬起来之后,依旧健步如飞。
潘邓对冯掌柜说道:“做得好,我见这担架妥帖。”他又看向军中虞侯,“这批军资送到军资库之后,先发放到吴指挥营中。”
那军虞侯点头应是。
潘邓又对吴指挥使说道:“以后在日常训练中加上担架运送伤员这一项,在每旬的考核中也把这项加上,全营考核,务必做到又快又稳,远程运送到军营,和咱们之前的项目一样,拿第一名的队伍有赏。”
吴指挥使拱手应是。
眼看那冯掌柜就要拉车与虞侯走了,张叔夜赶紧上前,“慢着。”
见周围人都看他,张叔夜捏捏胡须说道:“尔等还太年轻,把握不住其中关窍,还是让老夫检查一番。”
说着走向那担架。
远看是两边铁棍中间夹块白布,近看之后仍是白布,只是这布怎么这么硬!
其中的白布又硬又挺,紧密厚实,简直不像是布了,这一整张硬布左右各自围成一小圈,供中间的铁棍穿过,其缝合之处足有四排缝线,针脚细密,细看之下,竟然每针的间距都一样!
这是什么人能做出来的布?又是什么人能缝出来的线?早就听说东平府纺织一绝,今日可见一斑!
张叔夜又摸了摸厚硬的白布,呵呵一笑,放下担架,伸手挥开披风,走过去揽住潘府尹的肩膀,哥俩好地走到一边说道:“潘贤弟,老夫昨日与你定了甲胄、枪头和狼筅,如今若是再定这‘担架’,可还有优惠?”
潘邓笑着说道:“我听贤兄昨日所说,那三样已经将贵府掏空,哪里还有钱买这担架?”
张府尹闻言哈哈一笑,银披风随风飒飒而响,“常言道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老夫便以济州府尹之名,贷款买你这担架!”说完又是大笑不止。
潘邓:“……”
二人一边谈着担架之事,山上演习已经到达尾声,张叔夜又想看结果,不得不一边谈着价格的事,一边要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局。
蓝队在半山小路上拦截红队,但由于红队兵力分散,仍有小股部队绕过防线,接近蓝队后方,准备进行反击。
蓝队后方遭到突袭,留守后方的指挥使迅速组织队伍,前线都头加强攻势,牵制红队主力,红队主力在蓝队的强烈攻势下损失惨重。
蓝队又利用高地优势和密林中的伏兵,对红队进行包围,红队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利用河流作为天然屏障,成功阻挡蓝队的追击。
最终蓝队获胜,红队所剩十之一二,残兵败将逃脱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