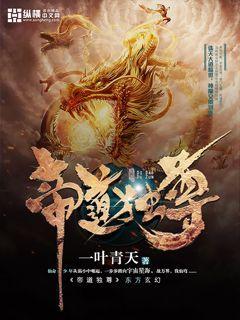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水浒]掀翻大宋 > 90100(第2页)
90100(第2页)
小郓哥说道:“纺织坊目前安好,月前冯掌柜已经将织女遣散回家,还有些人是无家可回的,只能留在纺织坊员工宿舍,冯掌柜又请了乡勇守卫,买了朴刀,每日结算工钱,驻扎四周。”
“那梁山宋大王放出话去不准侵扰百姓,但是还是有小匪头趁机作乱,抢劫好百姓,他们山上有个矮粗怪,听说了咱们纺织坊,非要来此吃喝,叫冯掌柜接待,李大官人得知此事,及时赶到,与那头领打了起来,后来他们上山,此事才了结。”
“无耻之徒!”李安澜骂到。
“三店和书坊歇业,大门紧闭,掌柜的和伙计都聚在一起,互相照应,等待梁山撤兵。李大官人刚刚上山,又有钱财,在宋大王面前很有颜面,因此能护住产业。只是听说那矮粗怪也是那宋江的得力手下,颇受宠,还不知能支应几时,他叫我赶紧来东京和老大人寻主意,没想到潘哥回来了。”
两人看向潘邓,潘邓听小郓哥说完,心稍稍放下,说道:“此事有我在,三娘在东京照看产业,郓哥和我回东平。”
两人这才感到东家回来了,心中无比踏实。
潘邓当天进宫面圣,请放东平府。
赵佶一脸为难地看着他,“卿家快起,你这是做什么?”
“山东匪寇流行,臣愿意为皇帝分忧剿匪!”
赵佶扶着潘邓的手臂把他拉起来了,“卿家出使金国,前日才归,吏部给的任命还没下来,怎要自请外放?”
潘邓说到:“东平如今被山匪攻破,臣心中焦急万分,得知此时考课院冷清,无人愿去东平接任,自请前往,愿平定匪寇,为大宋江山牧守一方,为陛下效力,死而后已。”
东平出了反贼,皇帝哪有不急的?只是眼下没兵,东平府太守已死,又无人愿意去东平接任,只留个烂摊子给他。
见皇帝有意答应,潘邓恳求道:“只臣籍贯东平,按例不应去东平为官,恳请陛下特旨,臣愿以死效忠。”
如今潘卿家愿替他分忧,实在是忠臣良将。皇帝想了想,便也就应下了此事。
皇帝御笔亲书,任潘邓为东平府尹,可调济州,郓州两州兵力,彼二州须联合抗匪,不得延误。
这样的任命不符合标准程序,但是皇帝都下了亲笔,陈文昭眼看又是太师之才,考课院便与人方便,写了任命文书。
“说起来潘邓此人既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什么家世,只一介小民,真是得了一个好老师,又得了皇帝青眼,才能如此一步登天。”
考课院几人闲聊,“……竟然下放做了知府,我家亲戚二哥,在外多年,三年又三年,考课又考课,年近五十,至今也才是通判。”
“谁叫他出使有功,此任还只是外放,若是留在京城,有个相公老师,又得皇帝看重,更是前途无量。”
“做什么想不开去外放府尹呢。”
几人啧啧感叹,文书写好,盖下大印。
*
潘邓当天出宫就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去东平。
呼延庆得知此事特地前来找他,说道:“我有一族人名呼延灼,去年在我出使之时,前去梁山剿匪,被梁山劝降,如今上山当了反贼,潘大人便当时看在以往情分,且请照看族孙!”
潘邓紧忙将他扶起,“呼延兄弟何必如此见外?当时你我二人出使之事历历在目,不曾忘记,呼延兄弟是忠义勇敢之人,族孙必定也有忠义气节,只是被那梁山扣下,借其名行苟且之事罢了。待我扫平梁山,必将族孙解救,放还归家。”
呼延庆顿时红了眼眶,“潘兄弟此情我记下了,大恩必定报还!”
送走了呼延庆,潘邓又叫来李三娘叮嘱,“我不在东京时,细心照看产业,不必担忧东平之事,我明日便启程,届时有什么状况必定会告知你。”
李三娘点点头,叮嘱道:“东家千万保重。”
第92章离开京师
在开封府的最后一个晚上,潘邓去了师叔家里。
徐观知道他忧心东平府,劝慰他安下心来,“那山贼已放出话去不伤百姓,可见是做事留一线之人,你能诏安便把他们诏安了,不须沾染兵事。”
潘邓凑过去抱着他的腰,一直烦躁忧虑的心在徐观身边感到一丝宁静。
徐观由他抱着,心里也不舍,一边担忧,一边又不舍,此去不止剿匪,是要留在东平做府尹,三年才任满,要有多少日不见?徐观摸着他的发顶,说道:“此去不知何时能再见。”
等到再见之时,你还能否记得今日的情谊?
潘邓见他忧愁,抬起头来看他,轻声叫道:“观哥儿……”
徐观听他叫自己,低下头来要吻,动作一半停住了,叹自己和潘邓在一起久了,竟然听到他这么叫,就下意识的要吻他。
潘邓把他脖颈微微下压,亲吻上去。
此间两有情人在此痴缠,潘邓喘着气说道:“观哥儿,我的伤早好了……”
徐观轻轻摸向他腰间伤口,此处有疤痕,但是肌肤已经恢复柔韧,潘邓又去解怀中人的腰带。
徐观抿抿嘴,把登徒子的手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