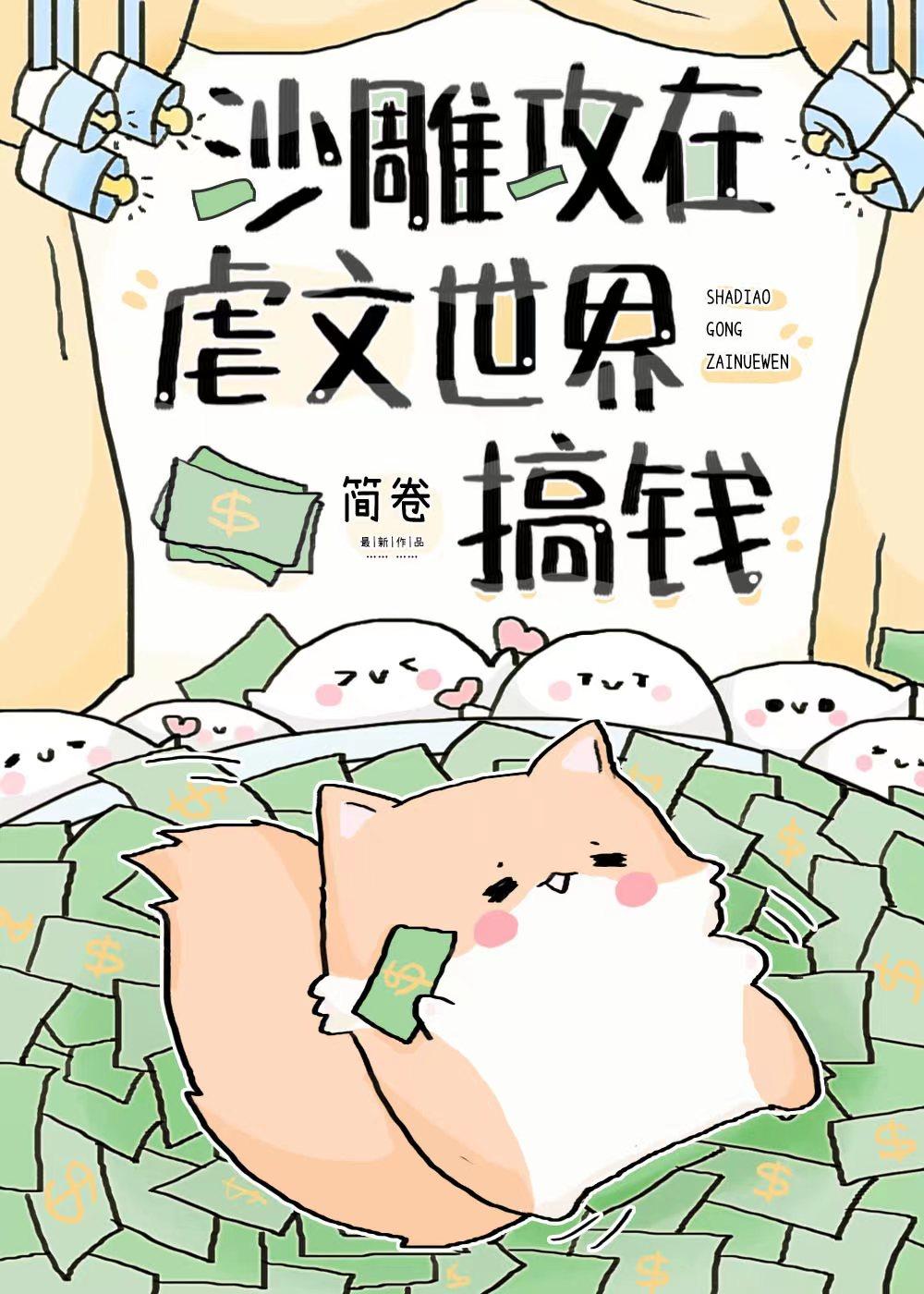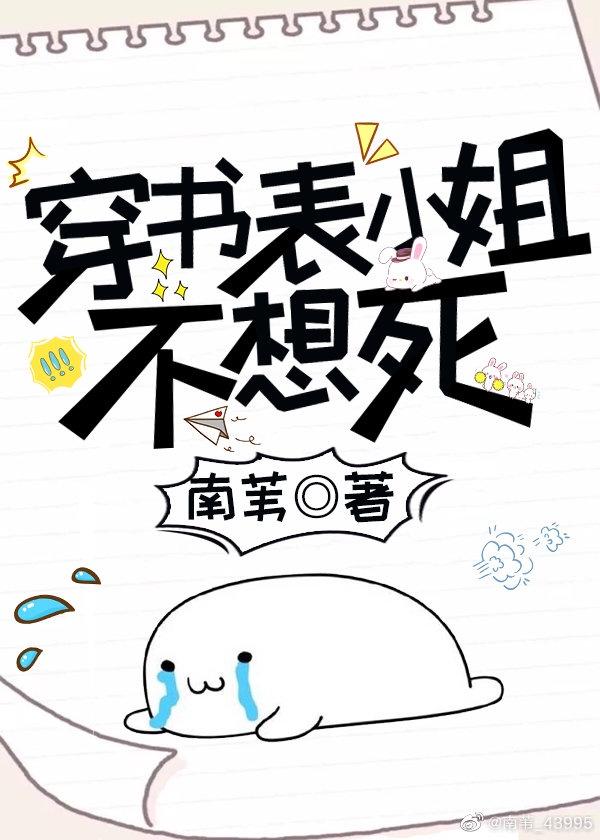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鸣珂 > 第195章(第1页)
第195章(第1页)
盛江海捧着披风没有说话,而是侧头望向无边的雨幕,阎止两人早已远的看不见了。他这一辈子都跟在皇上身后,记得不知多少年以前也是这样,目送着衡国公与漓王肩并肩地走远。只是不想故人如入雨幕,从此消失不见。
他年轻时也曾满心踌躇,以为明光近在眼前,却不知一脚踏入深渊,终至苦果难吞。哭声笑声,声声远去,都洇在绵绵的细雨中。
“哎,老东西,”皇上偏过头看他,“朕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
盛江海仍看着远处,笑了笑表示回过了神来:“依老奴所见,先帝在朝曾有猛虎吞人,陛下当政却已不见悍虎藏林,当真是安乐清平。”
雨势越来越大,顺着房檐哗哗地流落下去。书房外的芭蕉叶被打得弯了腰,落下的雨水越积越多,在院中的暗渠里汇成小溪,悄无声息地淌入池中。
漫漫的雨幕如一道珠帘,腾起层层的水雾,将天地也遮蔽住。
阎止回到平王府时众人都在,正坐在窗下围着茶炉说事。萧翊清肩上压着雪白的狐裘,身侧的窗用屏风挡了,只有落雨清润的气息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几人心中皆是舒展明朗。
封如筳起身给阎止倒茶,清淡的茶香与湿润的雨幕一起散开。雷晗铭与珈乌自兖州逃窜,贺容回北关报信之后,便留在锁游关值守,没有跟着回来。封如筳在回京的人群中没有等到想见的人,却收到了一封信,拿在怀里如获至宝。
他今日是来送卷宗的。杨淮英在御史台扣了七八天,是他亲自做的初审。这杨淮英滑溜得像泥鳅一样,是看准了他们手中没有实在的证据,一股脑地把罪责全都推给贾守谦,自己一件事都不认。
阎止捻着杯子思索着,漫漫的茶香抵不去案子的凝滞。兖州众多要事都经是贾守谦之手促成,即便杨淮英在背后主导唆使,他们手中确实没有证据。更何况,杨淮英身为二品大员,朝中人人都在盯着。虽说皇上下了谕旨容许他审,但关得久了难免物议如沸,届时如再起结党之争,只会对案情更不利。
但他反复思索并无头绪,不知该如何让其开口。
阎止把杯子放回桌上,只觉得手肘被什么暖烘烘的东西蹭了一下。周之渊在翰林院会逢大考,七八天都回不了家,干脆把宝团寄养到了平王府,一天三顿吃得富足。
宝团从桌下钻出来,伸着爪子去扒拉桌上的杯子。他把杯子拿远了些,猫肚子上全是暄软的肉,卡在桌子和人之间,杯子够不着,下也下不去,急得喵喵直叫。
林泓替萧翊清斟上温水,后者喝药,久不饮茶。他把壶放下,问封如筳道:“听说翰林院大考相当难啊,我上次见之渊,看着人都学瘦了。他说背书背的抓耳挠腮,我就让他去问问你。他找你了吗?”
封如筳说:“问了,得亏是翰林院跟御史台离得近,要不然还见不到呢。”
林泓期待地看着他,问道:“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封如筳神色莫名,摸了摸鼻子道:“我……我看一遍就记住了,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其他几个侍御史,他们也没碰到过,所以我建议他多背几遍——不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说的都是实话。”
林泓捂着脸叹了口气,其他几个人都笑起来。
两人禀完事就退下了,屋里又静下来。御史台的卷宗留在桌上,依然展着。阎止放松地将一侧的手肘支在凭几上,另一只手无意识地点着卷宗,阖目静思,窗外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
宝团在两人之间睡熟了,四脚朝天地仰着,尾巴时不时晃一下,又去勾着萧翊清的衣摆。
“凛川。”萧翊清在这细细的雨里低声开口。他整个人偎在榻上厚重的裘中,全然不似在盛夏。他拉了一下衣服,掩住从领口灌进来的风,只是微微抬了点头:“如何使杨淮英招供,我倒是有个想法。”
阎止问:“四叔怎么想?”
萧翊清道:“你不妨去问问户部侍郎,崔吉。”
户部在宫城外长街的最深处,一向是六部中最清净的地方。
只因户部尚书久为空悬,户部侍郎崔吉鲜少涉政事,一心扑在农事上,其他一概不理。各方软硬兼施地试探了很多次,纷纷铩羽而返,久而久之便随他去了。因此朝中暗有传言说,户部的铁门槛如同寺庙,进去了要么种田,要么算数,要么养活物,想干其他事情,迟早要被姓崔的扫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