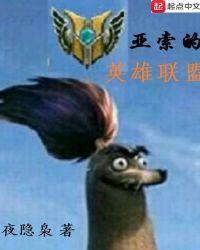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零七章 狗策划余惟(第2页)
第二百零七章 狗策划余惟(第2页)
余惟当场拿出录音笔,请她讲述过往。她讲得朴实,没有悲情渲染,只是陈述事实:怎么嫁给他,怎么熬夜炒茶,怎么在暴雨夜冒雨抢收,怎么看着第一批茶叶卖出后两人抱头痛哭。说到最后,她顿了顿,说:“我不是多伟大,就是觉得,有些事做了,就得做完。”
当天夜里,余惟在村支书家借宿,写下新歌《茶根谣》。
>“她说这山不是风景,是两个人的名字
>埋在每一株老茶树下,像心跳藏进泥土里
>外面人说她固执,说她跟不上时代步履
>可她知道,有些绿不会枯,哪怕无人采摘它的苦”
>
>“三十年施肥除虫,一个人走遍整片坡地
>手掌裂口结痂又撕开,从春到冬不停息
>当收购商终于开着卡车来,问她要不要涨价卖地
>她摇头:这片叶子,只配泡进劳动者的杯子里”
他将音频传给陈屿,附言:“我想把它送给所有坚持到最后却无人喝彩的人。”
一周后,他抵达四川凉山深处的一个彝族寨子。这里通讯几乎断绝,手机无信号,电力供应不稳定。寨老听说他是“那个唱歌的汉人”,亲自迎出寨门,用古老礼仪献上羊毛披肩。
当晚篝火晚会上,余惟被请上坐。年轻人跳着传统舞步,老人在一旁弹月琴。酒过三巡,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起身,颤巍巍走向他,递上一只布包。
“这是我孙子写的。”她用彝语通过翻译说,“他去年考上大学,是村里第一个。临走前夜,他写了这首诗,说要是遇上你,就请你唱出来。”
余惟打开布包,是一张皱巴巴的作业纸,钢笔字歪斜却用力:
>《父亲的背》
>
>父亲的背是弯的
>像门前那棵老核桃树
>他背着土豆走三十里山路
>换来我的课本和铅笔
>
>父亲的背是硬的
>能扛起整个家的重量
>台风刮倒房屋那天
>他用脊梁撑住横梁直到天亮
>
>现在我要离开大山了
>可我知道
>他的背再也直不起来了
余惟读罢,全场寂静。他接过月琴,略作调音,以最简单的和弦伴奏,用汉语缓缓吟唱。歌声一起,许多村民低头啜泣。那位老妇人跪坐在地,双手合十,像是在接受某种神圣仪式。
那一夜,他明白了一件事:艺术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技巧多高超,而在于是否敢于承载他人生命的重量。
![受气包她不干了[快穿]](/img/504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