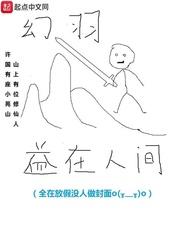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天赐良缘[GB] > 第47章 以身殉职(第2页)
第47章 以身殉职(第2页)
“遵命。”暗卫话音未落,身影已消散在黑暗中。
应慈怀看向外面的雨幕,自言自语:“好啊,这雨下得好啊。惧水哈哈哈,老天都在帮我们。”
贺遥苏醒时,已是次日深夜。喉咙火烧般疼痛,发不出半点声响,只能勉强敲击床榻。
“公子!”守在屏风后的书谨闻声扑来,见贺遥唇形翕动,急忙奉上茶水。
贺遥虚弱摆手,书谨凑近辨认,才看清那无声的呼唤是“卫疏”二字。泪水顿时夺眶而出:“大人她……已经……尸首正运往京城……”
贺遥如遭雷击,重重跌回床榻。
泪水决堤般涌出,他挣扎着以气声追问:“到底怎么回事?”
书谨颤抖着点燃灯盏,将誊抄的文书举到贺遥眼前。
贺遥每看一行,泪水就汹涌一分,喉咙里发出破碎的抽气声。
“砰”地一声巨响,房门洞开。
“遥儿!”卫展嵘带着医师疾步而入,双眼红肿如桃。
贺遥泪眼朦胧地望着卫展嵘,固执地摇头。
他拼尽全身力气想要起身,却像断线的木偶般栽向地面。他要去见她,哪怕爬也要爬到浦州。
卫展嵘一把拽住他,声音嘶哑:“你高热未退,先让医师诊治!”
见贺遥仍在挣扎,他猛地将人按回床榻,厉声道:“遥儿!疏儿下落不明,阿灼被困在宫中,公主府现在只能靠你撑着!”
这句话如冷水浇头,贺遥终于停止挣扎。
他木然地躺回去,任凭医师把脉,泪水却仍如泉涌,浸湿了整片枕席。帷帐在他泪眼中模糊成一片惨白,就像他此刻支离破碎的世界。
卫展嵘下令,派人轮班守在贺遥房门外。
皇宫那边,应煜提着雕花食盒踏入寝殿,殿内沉水香的气息浓得几乎凝滞,唯有应灼身上淡淡的柏子香能冲淡这种气味。
应灼单薄的身影倚在龙榻边,背脊不再如往日那般笔直,像一柄被岁月折弯的宝剑。
他走近了才惊觉,一夜之间,她鬓边竟已生出丝丝银白,在宫灯下泛着冷光。
“长姐可看过浦州急报了?”应煜将食盒轻轻搁在案几上,明知故问。
应灼纹丝未动,目光仍锁在应连恒青灰的面容上。
“疏儿以身殉国,死得其所。”
“若陛下清醒,定会追封卫疏为……”
“当年毒害皇兄,用的也是这种手段吧。”应灼突然打断,声音像淬了冰。
应煜眉梢一跳:“长姐此话何意?”
淅沥雨声敲打着殿外的雨棚。
应灼缓缓起身,锦缎裙裾拖过金砖,发出细碎的声响。
“自入宫侍疾首日,你便说我们三人皆在寝殿,空间狭小,让皇帝将长箭移出殿外。”
她停在朱漆门槛边,回眸时眼底寒光乍现,“是怕自己也染上魁油之毒?”
应煜指节泛白:“长姐痛失爱子,难免神思恍惚。”
应灼唇角勾起一抹冷笑,“满朝都说你思念皇兄成疾,可你自己最清楚——”
她突然逼近,凤钗珠串叮当作响,“唯有借着悼念先帝的名头,才能赚得这贤王美名。”
应煜警惕地盯着应灼,虽说卫星朗死了,可应灼的手段,从来凌厉。
应灼走出殿,声音渐远:“该你守夜了。就当我是糊涂了吧。”
柏子香渐远,应煜忽然有些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