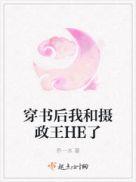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贫道要考大学 > 第166章 狡诈冰块精你等着(第3页)
第166章 狡诈冰块精你等着(第3页)
“我们在地基下挖出了三块石碑,刻着‘灵应观重修记’,年代为嘉靖十二年。其中一块提到了‘青囊三卷,藏于东厢夹壁’……你家里有没有相关记载?”
陈拾安心头剧震。
当晚,他带着工具回到废墟,在当年父亲卧房的墙角摸索许久,终于撬开一块松动的砖石。里面藏着一只陶罐,封口完好。打开后,赫然是两册泛黄手抄本,墨迹苍劲:
**《青囊经?卷四:脏腑真源论》**
**《青囊经?卷五:九针秘要图》**
他颤抖着手翻阅,泪水滴落在纸上。
原来,传承从未断绝,只是埋得足够深。
他立即联系谢云昭,并附上高清扫描件。三天后,回信抵达:“国家古籍修复中心愿意协助整理,条件是你担任学术顾问,并允许部分内容用于科研验证。”
他回:“前提是,所有成果必须标注‘源自民间医者代际传承’。”
协议达成。
春节那天,全村再次聚宴。这一次,不仅是庆功,更是祭祀。他在灵应观遗址前设坛,焚香祭祖,将两册新出土的《青囊经》副本供于案上。
温知夏站在身旁,轻声问:“以后打算怎么办?”
“一边学医,一边整理这些资料。”他说,“等博士毕业,我想回来建一所‘传统医学实证研究所’,就在这儿。不用豪华大楼,只要一间教室、一间药房、一个数据采集室。教年轻人怎么看脉象,也教他们怎么写论文。”
她看着他,忽然笑了:“那你得赶紧考医师执照。”
“我在准备。”他握住她的手,“等我穿上白大褂的那天,你就嫁给我,对吧?”
雪落无声,她靠在他肩上,轻轻“嗯”了一声。
正月初八,他重返北京。临行前,将《卷四》《卷五》原件锁入檀木盒,贴身携带。火车启动时,他最后一次回头,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温知夏站着挥手,怀里抱着猫儿。
他知道,这条路上会有无数质疑:
“一个道士懂什么分子生物学?”
“中医能发SCI吗?”
“别把玄学带进实验室!”
但他不再辩解。
因为他已懂得,真正的光,不是用来照亮别人的,而是让自己在黑暗中始终看得见路。
列车穿越隧道,又见光明。
他打开电脑,新建文档,命名为:
**《青囊新编?序》**
>“余承父志,习道问医,深知古法非敝帚,科学亦非金科。
>今以六年寒窗之约,立此宏愿:
>使每一味草药都有成分图谱,
>每一条经络都有信号轨迹,
>每一句‘气虚血瘀’都能被机器读懂,
>而每一个坐在诊室里的病人,
>既能得到最先进的治疗,
>也能听到一句温柔的‘你最近,是不是很累?’
>
>此书不成,不敢言归。
>此道不灭,终将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