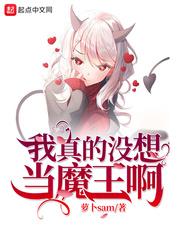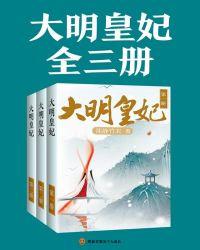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二百五十二章 汉土(第1页)
第二百五十二章 汉土(第1页)
“我一生使用了太多的阴谋诡计,这是道家所禁忌的。
我的家族世系可能从此废黜,无法再兴盛起来,这是我积攒了太多阴祸的缘故。”
陈平临终之际如是评价自己。
陈家命运似乎与陈平预言一般,一。。。
风雪夜,长安城外百里驿道上,一骑黑马踏破冰霜疾驰而来。马背上的骑士披着黑斗篷,面罩寒纱,只露出一双冷峻如刀的眼睛。他腰间悬剑未出鞘,却已透出杀气凛然。抵达函谷关前哨时,守将认出那枚嵌有青玉螭纹的令牌,急忙跪地迎候:“属下参见‘玄甲’使者!”
骑士不语,仅抬手递出一封火漆封缄的竹筒。守将双手接过,拆开一看,脸色骤变??上面赫然是太子亲笔所书八字:“令发即行,勿问来由。”
“遵命!”守将咬牙叩首,转身传令:“关闭关门,截查一切自陇西返京之使节!凡携密信者,格杀勿论!”
与此同时,未央宫东偏殿内,刘彻正批阅奏章。案头堆满各地上报的祥瑞灾异、赋税钱粮,但他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份不起眼的边报上:**“匈奴右贤王部近日频繁调动,似有南侵之势。”**
他冷笑一声,掷笔于案:“李广利奏匈奴求和,如今又说其兵马异动?莫非真当朕老糊涂了?”
侍立一旁的张汤低声进言:“陛下明鉴。臣细查往来文书,发现匈奴使团所献牛羊中,竟夹带有西域精铁锻造的短刃数百柄。此非求和,乃示威也。”
“果不出吾所料。”刘彻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漫天飞雪,“刘据啊刘据,你勾结外敌,煽动诸侯,连匈奴都成了你的棋子。你以为朕不知?你以为天下还能容你逍遥?”
张汤犹豫片刻,终是开口:“陛下,若太子真与诸侯密谋起兵,恐需早作部署。北军五营之中,羽林左监李广成、屯骑校尉程不识皆曾为太子旧部,不可轻信。”
“那就换人。”刘彻眸光如电,“即刻召霍光入宫,授其‘监国中尉’之职,统辖未央、长乐两宫卫戍;再命金日?率胡骑千人屯驻建章宫外,名为护驾,实为控兵。”
“唯。”张汤领命欲退。
“等等。”刘彻忽然止步,“传吾口谕:明日午时,宣群臣于白虎殿议事,议题只有一个??废除太子讲经日制,改设‘幼主习政仪’,由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列席观礼。”
张汤心头一震,知这是公然挑衅太子权威之举。他低头称是,悄然退出。
夜更深,风更烈。
东宫深处,刘据仍端坐书房,面前地图已被重新绘制,新增数十红点,皆标注为“可募义士”“可藏兵器”“可断粮道”。一名蒙面女子悄然推门而入,单膝跪地,声音清冷如泉:“启禀殿下,七国回应已至。淮南王承诺举兵三万,齐王愿献战车五百乘,燕王则密约乌桓骑兵二千,可越长城直扑渔阳。”
刘据点头,淡淡问道:“吾丘寿王那边可有动静?”
“有。”女子取出一枚铜符,“昨夜子时,他派人送来此物,并附语:‘血诏已动,天网将开。’”
刘据凝视铜符良久,终于展颜一笑:“好一个吾丘寿王……表面忠君,实则步步为营。他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等天下共讨昏君的那一天。”
“殿下,”女子迟疑道,“若您真要起事,是否该先控制未央宫?玄武门虽险要,但一旦父皇闭宫不出,恐难速决。”
“不急。”刘据站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一幅古画前,轻轻揭开??竟是整座长安城的立体沙盘,山川河流、街巷坊市、军营仓廪尽在其中。“父皇以为我在争权,其实我在等势。当他逼我至绝境,当我被迫‘造反’,天下人才会看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
他指尖缓缓划过沙盘上的未央宫南阙,继而北移,最终停在玄武门之上。
“那一日,我不只要夺门,更要定鼎。”
风雪交加的第五日清晨,长安城迎来了罕见的朝会大典。
白虎殿前,文武百官按品列队,气氛肃穆得近乎诡异。董仲舒手持玉笏,立于左班首席,眼中闪烁着难以掩饰的亢奋。他知道,今日将是彻底动摇太子地位的关键一步。
钟鼓齐鸣,刘彻驾临。龙袍加身,冠冕垂旒,帝王威仪震慑四方。
“诸卿。”刘彻开口,声如洪钟,“今岁彗星现,天象示警。或曰储君失德,或曰朝纲不振。朕思之再三,以为国本不可轻摇,然教化亦须更新。自即日起,废太子每月讲经之制,改为‘幼主习政’,由皇子弗陵随朝观礼,学习治国之道。”
此言一出,满殿哗然。
太子讲经,乃是昭示储君德行、凝聚士林人心的重要仪式。如今骤然废止,无异于公开宣告刘据失宠。更令人震惊的是,年仅六岁的弗陵竟被推上前台,俨然已有立嗣之意!
太常卿孔臧当即出列,颤声道:“陛下!太子仁孝恭俭,百姓称颂,岂能因天象而轻废国本?且《春秋》有云:‘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年。’今皇后虽逝,然太子乃卫氏正统,岂可轻易动摇?”
“住口!”刘彻怒喝,“尔等儒生,只会引经据典,可知天下艰难?朕为江山计,岂容尔等妄议!”
就在此时,右班中一人缓步而出,正是吾丘寿王。他躬身一礼,语气平静却不容忽视:“陛下,臣有一言,或逆龙鳞,然不得不发。”
刘彻眯眼看他:“讲。”
“太子讲经,非仅为学,更为天下表率。今骤然废之,恐伤士人之心。不如暂行‘双轨并行’之策:既令幼主观政,亦许太子每月讲经一次,以安众望。”
董仲舒闻言大惊,欲出言阻拦,却被身旁重臣悄然拉住袖角。他猛然醒悟??吾丘寿王此言看似调和,实则为太子保留一线正统象征,是在为日后翻盘埋下伏笔!
刘彻沉默良久,终是冷冷道:“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