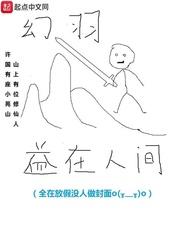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昭雪引 > 审问驸马(第2页)
审问驸马(第2页)
薛文寅陷入深深的自我纠结:“我不知道究竟是药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啊!她好好的,突然那样了。我只是想让她在鸿胪寺出丑,在朝会上,在陛下面前失仪,毁了她的仕途,就像她当初对我做的那样而已。我是真没想到,我不是真的想害她性命啊!”
裴昀与沈知意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看到了凝重。这案子果然有疑点!
驸马反复念叨着:“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想毁了她。”“定是有人害我!”
沈知意眼中闪过一丝不忍,眼看着就要有新的线索了,她耐住性子问薛文寅:“你还记得卖给你药的术士,长什么模样吗?”
驸马脸上重新出现茫然之色,仿佛思绪被拽回了半个月前,带着不确定的飘忽:“大概五六十岁?不对,应该二十来岁。”
“到底几岁?”裴昀的目光锐利如鹰隼,紧紧锁住驸马,“长公主之死你难辞其咎,但你应当知道,倘若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蒙蔽的,你也应当找出幕后凶手,这是为了你自己的良心!”
驸马一愣,半晌,颓然坐在地上,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我不知道。”他道,“那个人脸上满是皱纹和沟壑,但递给我药时,手上却光滑地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急着拿药离开,并未细究。”
裴昀闻言皱眉,世上有这种奇特的人吗?
“那五官呢?”沈知意立刻追问,“你能画下来吗?”
裴昀闻言,沉声喊道:“来人,拿笔来!”
很快,狱卒便送来了纸张和笔墨,在裴昀的命令下,递进了牢内。
驸马颤抖着抓着毛笔,像是抓住了生的希望。
他努力稳住手腕,凭着记忆在纸上勾勒起来,笔触时而深浅不一、时而歪斜,但探花郎的底子仍在,很快便勾勒出了个大概:
果然如驸马方才所说,满脸的褶皱、是个老年人形象,一张脸上鹰钩鼻尤其明显,一双眼睛又小又凹陷,看着十分诡异。
看着纸上的线条,扭曲怪诞,几乎难以称之为“人”的形象。
她与裴昀面面相觑,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惊讶。
驸马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这一遭下来,便瘫软在地,眼神也更为涣散开来。
裴昀与沈知意两人相顾片刻。裴昀打了个出去说的眼神,两人沉默着走出阴森压抑的大理寺狱。
“你怎么看?”刚出得大理寺狱,裴昀便问沈知意的看法。
沈知意却难得地摇了摇头,“没什么头绪,但按照驸马所说,我们得找到这个人!”
她指了指裴昀手上的画像:“可是,这能是个人吗?哪有人同时有着老年人和年轻人共同的特点的?还长那么渗人。”
“我会让魏寺丞去查的,只要这个人出现过,总会有些线索。”
“希望吧。”沈知意叹了口气。
裴昀“”嗯“”了声,神情格外凝重,难得的没说话,神思不属地直直往前走,倏然,人顿在了原地。
怎么了?
沈知意不出意料地透过他的视线往前看,就见一队身着宫装的女官往公主棺椁停放的方位走,应是去为公主收敛了。
不多时,沉重的锣鼓声响起,一下,又一下,缓慢而压抑地敲击着。
长公主的棺椁被抬到了长安城的长街之上。
长街上,早已正式净街。
一个个身穿玄甲、手持长戟的金吾卫肃立如林,像一堵人墙,隔绝了所有窥探的目光,宽阔的街道上鸦雀无声。
素白的幡帐在凌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发出悲鸣般的呜咽。
长公主的棺椁在力士的肩扛下,沉重地压过冰冷的石板路,朝着荐福寺的放向行去。
白幡招展、纸钱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