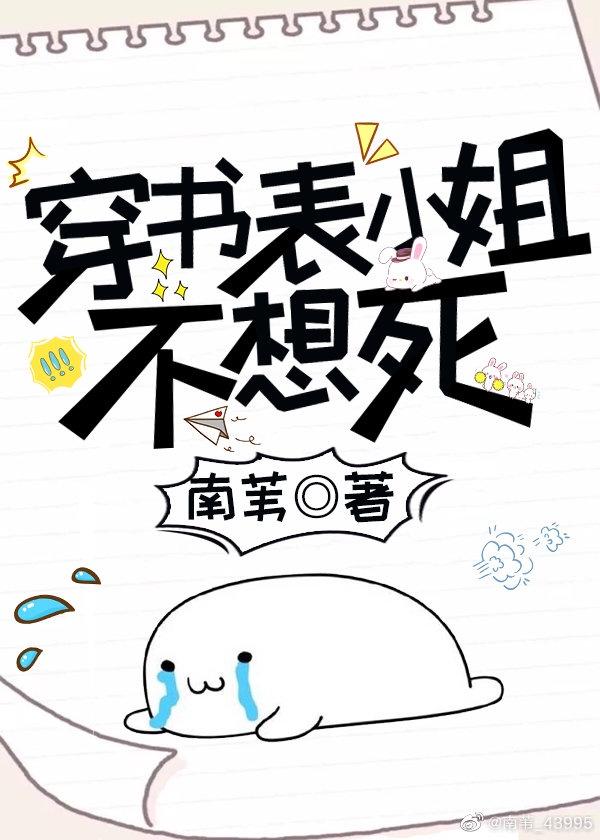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水滸开局在阳穀县当都头 > 第309章 末將知罪末將知罪啊末將来日(第4页)
第309章 末將知罪末將知罪啊末將来日(第4页)
“渠帅想好,此番城池一开,可就没有退路了!”许贯忠真不催促,反而好似设身处地为郭药师去想。
郭药师从来不傻,也不是隨便他人忽悠之辈,只是眼前之局……
也有个眼前,当面之事,就在眼前,愿意也好,不愿也罢,怎么办呢?死守城池,短时间內,可真无人能救他……
更何况许贯忠说得句句在理……
“走!先生前请!”郭药师抬手一比。
“看来渠帅是篤定了,那就走吧……”许贯忠自往前迈步。
最⊥新⊥小⊥说⊥在⊥⊥⊥首⊥发!
不得多久,城门真开,许贯忠打马走前,郭药师打马在后,百十骑而出,城內岂能没有女真人,但此处不同,少量女真人没有意义,只管拿了就是。
苏武打马就在城外,那郭药师快马就来,马不停,人已然翻身而下,当面立马就跪:“相公恕罪,末將该死,千言万语,皆是末將一时猪油蒙心!末將该死!”
苏武俯视去看,没有说话,面色铁青,目光也冷。
郭药师自是头也不抬,等著……等著发落!
许贯忠立马上前来说:“相公,自也不能全怪郭渠帅,著实是谭稹与王安中不当人子,那平州张觉之事,办得是天怒人怨啊……”
苏武冷冷一语去:“起来吧,你献了城池,我总也不能还將你杀了去,否则来日,何人还能献城?”
“末將知罪,末將知罪啊!末將来日,定当百死!”郭药师连连磕头,还不起身。
“哼哼……”苏武冷冷一笑,管那郭药师起不起来,打马往前就走,入城,而今,城池格外重要,面对女真之骑,一个一个的城池,就是苏武的倚仗。
郭药师一脸焦急,这个时候,城池都出来了,却只换来苏相公两声冷哼,岂能不急,连忙往旁去看:“许先生,这般如何是好啊?相公不信我也!”
许贯忠稍稍摆手:“无妨无妨……渠帅不急,头前过涿州,多少兵马在守?”
“涿州倒是有数千兵马,皆老弱之辈,女真数百……”郭药师来答。
“先登,数百女真,倒也够,渠帅先登!渠帅但凡捨命先登,相公自就高看一眼!”许贯忠如此来说。
“那那……”
“不急,还有燕京城,燕京城內,想来女真至少一两千去,渠帅以往就破过燕京城墙,此番再来一次,相公当倚为心腹!”
许贯忠岂能没有办法?
“当真?”郭药师问。
许贯忠认真点头:“自是当真!”
“那……那好!”郭药师也是咬牙,麾下兄弟,此番怕是要折损不少了,但为了將来,总要捨命一番,本就是活不下去的人成的怨军……
干吧!
许贯忠正说:“渠帅速速回军中去,激励军心,死战一番!定不要让我在相公面前失了脸面。”
郭药师这才从地上起来,点头拱手:“我自去也,先生放心!”
说著,郭药师翻身上马快奔,是要与兄弟们交心一番,这回,可真就没有退路了。
入城去,苏武自去府衙理事,麾下军將,也当休息一番,补给一番,饱食一顿。
许贯忠站在当面,微微笑道:“相公那两声冷哼,当真是好!”
“你我,不谋而合罢了……”苏武也笑。
“与相公谋事,当真省心!相公高明。”许贯忠再夸。
“是先生高明!”苏武也夸。
“嘿嘿……相公,如此就不必再等王稟將军了,可速克涿州与燕京,可命刘光世將军往南去,去克雄州,雄州坚城,可阻挡女真过昔日宋辽边境,如此,许在雄州,女真就要舍下不少东西……再命姚平仲將军往檀州,守得胜口、古北口关隘。刘正彦將军去营州,守住榆关,还有重中之重文德城,鲁达將军带吴玠吴璘去。如此,燕山一线,大缺口皆堵得严严实实……”
许贯忠慢慢来说。
苏武只管点头,却还问:“燕云诸城呢?”
“燕云诸城,多不必管,本就被女真蹂躪一空,百姓不是被掳掠,就是多有逃散,城池里也无钱粮补给,只管燕京、涿州、弘州、奉圣州四处,燕京自是相公坐镇,弘州让大同王將军一併来管,奉圣州,本就是文德城周近,自是鲁达將军来……”
许贯忠说到这里,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