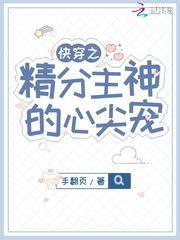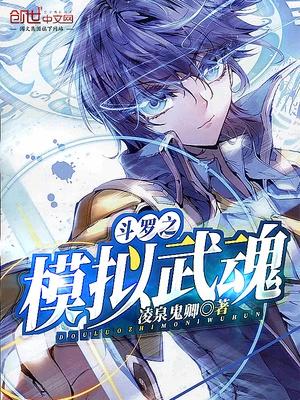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江湖与彼岸 > 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上(第2页)
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上(第2页)
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
苏:是的,那本杂志办在湖北。实际上就是说,你在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是不只是诗歌本身的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86大展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徐敬亚、吕贵品等人外,你和孟浪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算是为现代诗呕心沥血了。你在深圳摔碎了牙齿和下巴是在大展之前还是大展之后呢?
朱:在大展之前。当时趁我老爸出差的便利,我也跟着去了,老徐搞了个深圳现代青年诗人协会,我就是赶去参加成立大会的那个仪式。当时孟浪在深圳大学,深大还有几个大学生诗人,其中就有后来比较有名的蓝蓝,他们几个人邀请我去深大做一次演讲。当天白天先去蛇口看一个朋友,他说你骑自行车去演讲,晚上回来到我这儿住,可以好好聊聊。当时深南大道还没有完全修好,我骑车骑得非常猛,没有指示灯,结果一下子车掉到工程地沟里,整个下巴前冲式地撞到车把上了,哎呦,十几分钟是蒙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知觉了。那个沟大概有三、四米深,自行车掉进去了,幸运的是我没有掉进去。逐渐清醒后,我从身上摸出打火机,先找到把眼镜,突然感觉满口都是牙,牙齿全都松掉下来。好在随身带了一本香港出版的现代西方绘画史,花了我五十多块钱,尽管很是心疼书,但没有办法只好把那本书撕了,一边擦血,一边把自行车拎上来。骑车回去找我那朋友,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的朋友家。
苏: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
朱:初来乍到的,根本不知道医院在哪里,首先的想法就是找到朋友。朋友推门一看,以为我被抢劫了,我又说不出话,就报警了。到了医院,需要立即手术,蛇口医院的大夫说,要是手术的话就破相了,因为要从两个耳朵把下巴掀开,我那哥们说这可不行,他是著名诗人怎么能够破相!蛇口医院说,那就送深圳市区吧,到达深圳人民医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开始做手术,整个手术没有使用麻药,我的整个身体痉挛地进入幻觉状态,真的是疼昏过去了。我当时兜里没带钱,医院给老徐打电话,老徐、王小妮、吕贵品来看我,他们第一个反应以为我喝酒喝多了,来的时候竟然还带了几罐啤酒。我住了一个月的院,整个牙齿被铁丝裹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些流食。
寻找生命和语言一体化的表达方式
苏: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回牡丹江在北京中转时,不是在我的宿舍煮了鸡汤嘛。其实诗歌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是在灵魂上,在肉身上也一样留有痕迹。诗歌没有给我们这些人带来所谓的名利,相反为之付出太多的代价,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一件接着一件,包括你满地找牙的身体损伤。我们现在再谈谈牡丹江,除了你在深圳、北京等地的诗歌活动,更多的时间你是在牡丹江,可以想象在完全封闭的偏僻一隅,当年你的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呢?
朱:我在牡丹江一直保持与全国各地的地下诗人书信的联系,源源不断地收到自媒体的油印诗刊,后来是铅字诗刊,按当时的说法都是非法出版物。牡丹江很偏僻,也没有现代诗的氛围,但我通过杨川庆结识了时任《牡丹江日报》副刊编辑的宋词,后来我和他一起以“体验诗”参加86大展,并成为一生的朋友。应该说,宋词以前是写抒情诗的,跟我结识后转向现代诗。我们共同在牡丹江来推进周边的艺术活动,把当地的几位画家、摄影家凑到一起成立了局外人俱乐部,抱团取暖。
苏:我曾在韩博的一篇短文中了解到你和宋词在牡丹江的艺术活动。
朱:我认为在现代主义诗歌活动中自己终于找到了现代诗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及跟自己生命本体意识契合的诗歌形式,你不是总说我凭借一首诗闯荡诗歌江湖吗,就是当年写的《空位》这首诗,我也认为这是我第一首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诗的诗。它标志着生命跟语言找到一体化的表达方式,完全超越了先前古体诗或者是西方翻译文学对我的影响。
苏:能不能这么说,一个诗人成熟之前会有很多练习之作,你在《空位》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你的练习本?
朱:可以这么讲,《男子汉宣言》、《太阳岛上》等诗作是搭上校园诗歌的最末一班车,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和校园诗歌是不同的,大多数校园诗的表达方式倾向于情绪化的唯美,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体验感觉。
苏:那么可不可以说,《空位》是你真正进入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标志?大展之后,你的作品好像比较集中地发在《作家》、《关东文学》等杂志上。
朱:我那时在官方的杂志上基本没有发表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丑小鸭》能发表一点现代诗,所以我给《丑小鸭》投过稿,发过两首还是一首,想不起来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诗。
苏:应该不是,长春的《青年诗人》在我们读大学时曾以“大学生诗歌”专栏的形式发过你的诗。
朱:我想起来了,那个《青年诗人》杂志的主编是何鹰,当时我还拜访过他,他从我们的《北方没有上帝》每个人摘取几首诗做了一个专栏。1986年以后,有了老徐的这个现代诗大展,自己的诗歌也进入了现代诗的写作阶段,所以开始关注各种杂志。有一天偶然收到《关东文学》,发现这个杂志居然在做现代诗,而且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当时还觉得蛮惊喜的,所以就给它投稿。当时它的主编是宗仁发,后来是《作家》的主编,是一脉相承的。我和这两本杂志联系密切,曲有源当时是《作家》的诗歌编辑,宗仁发是主编,他俩和徐敬亚、孟浪、还有我曾想编一本《现代诗年鉴》。
苏:好像我听你说过,后来不了了之了。
朱:我们当时写了征稿信,每个人写了一段话,给全国发出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了了之了,没出来。
苏:印象中你在黑龙江也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
朱:我属于墙外开花墙内红。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之后,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在《诗歌报》发评论,获得一点名声。
要做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诗人
苏:那个年代诗坛上既写诗又写评论的人不多,你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你和包临轩联袂写过一篇文章《疲惫的追踪》,是批评谢冕先生的,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会写这样一篇文章,那个年代谢冕是新诗潮的引领者,是中国现代诗的理论家,为什么要朝他开刀?
朱:这是很偶然的事件,去北京出差除了看你之外,当时北大一个五四文学社,张华锋是当时的社长。之前我见到西川,印象很深的是,他请我吃了一份西式的西红柿拌饭。旅居瑞典的诗人李笠那天也在北大,当时我希望张华锋和李笠引见我去拜访谢冕,其实见谢冕,某种程度上比当年见老徐还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正像你说的他是朦胧诗的推手,对现代诗不遗余力的支持。但是去他家里拜访的时候,交流发现其实他对朦胧诗有一定了解,但对我们后来的这些年轻诗人,即所谓第三代诗人的生活方式、诗歌语言特点等等并不是有很深入的了解。说句不客气的话,好像他想维持自己教父的地位,不得不收集这群人的信息、作品、想法,再去写相关的评论。我觉得他已经过气了,已经抓不住现代诗的真实脉络,不真正了解第三代诗人,尽管他的愿望是良好的,他想保护、鼓励甚至宣传这群人,但我认为他已经远离了我们,所以当时就产生批评他的这种想法。我找到包临轩,我们俩共同完成那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据说反响很大,很多人包括你也觉得谢冕对我们这代诗人是真心的好,这么鼓励我们,现在就开始批评他,有些过分了,听说他的一些研究生很愤怒,想找到我,揍我一顿。
苏:我与谢冕先生接触得多一些,更了解一些,你和他只是匆匆见上一面,时间那么仓促,交流不会特别充分,其中必有误解。
朱: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敢抡,对不对,自己要做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自己想说就说了,包括后来说PASS北岛。
苏:你那个时期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也写过几篇我的诗论,在《深圳青年报》,以及你所在的《牡丹江日报》都发过。在你的这些理论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三代诗论》,这是一篇比较早的关于第三代诗人的理论文章。
朱:关于第三代诗人,我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应该是1985年的《第三代诗论》,在《深圳青年报》发的,后来在《诗歌报》上发的,是1986年写的,,叫《第三代概观》,后来一些海外华人报刊也相继转发,实际上是两篇文章。第三代诗是四川那帮人提出来的,应该是万夏他们的现代诗交流资料还是整体主义,反正是民间诗刊提出了这个第三代诗。我当时是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认为他们提这个界限分界是有问题的,他们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划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界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要划分三代诗歌,第一代现代诗应该是五四前后那一代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人,当然包括胡适这一批人,他们才是真正现代诗萌芽的这批人;第二代我认为是朦胧诗;然后才是第三代诗。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诗人数量最多的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诗人群体,我想把全国的这个格局尽我的可能和了解把它梳理和呈现出来,所以写了这么一个《第三代诗概观》,当时在诗坛还是蛮有影响的。
苏:第三代诗的整个过程需要理论的支持,你的文章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需要,应该说是恰逢其实,对第三代诗人迅速发展壮大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呢,凌波,我个人觉得大展的准备还是有些仓促的,人员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任意性,是吧,实际上遗漏了不少优秀的诗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展对后来甚至一直到天,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进一步了解的是,大展之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必须回到日常生活的状态。
朱:大展确实让我们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大展过后,我们也在反思,包括老徐他发起这个大展,后来他和孟浪、***,吕贵品编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实际上就是大展诗歌的结集嘛,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补充。沉积以后我开始想自己的写作之路到底怎么走,所以大展之后一直到1989年的这段时间,确实还真的沉下心来写了一些现代诗。如果从个人创作来说,这段时间对我是很重要的,真正扎扎实实沉下来,而不是作为一个诗歌活动家活跃于社会性的活动和群体性的活动。应该说,我找到了表达自身生命的痛苦虚无的真正的现代语言。
写作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苏:也就是说大展之后你的诗歌写作完全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你的《空位》是一个标志,或者说是你个人写作的一个高度或标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朱:1986年以后,我的两组诗是这段时间比较代表性的,一组是1988年的《冬天的火焰》,发在《北方文学》上,还有一组是写于1989年的《最后一个年代》,这两组诗是我个人属于现代诗的比较重要的作品。
苏:说实话,我对你当年频繁的活动和近乎于串联性的诗歌交往是保持警惕的,它除了对壮大名声有好处,不会对诗歌写作有益处。你还记得吗,你每次途径北京住在我的宿舍总是很晚回来,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可谓是殚精竭虑了。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安的,而且是主动的疏离、疏远,坚持安静写作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你简直就是处于疯癫状态,北京还有你没见过的诗人吗?除了北京、深圳,你好像到处参加诗歌活动,包括上海你也去过,见了舒婷,舒婷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不要玩熟手中的鸟》。我的印象里到处都有你在,你是完全作为一个诗歌活动家,问个其他的问题,那时有没有官方找过你,比如希望你加入协会啊。
朱:其实真正去的现场并不是很多。当时我在银行工作有出差的便利条件,有时候老爹出差我也跟着蹭,主要就是深圳、北京、上海这么几个地方吧,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去过。在上海见到舒婷,还有北岛、宋琳,马原等人,但跟全国现代诗人的书信往来是频繁的。那时在南方有几大诗歌阵营,一个是四川,一个是上海,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属于在野派,不像复旦大学、华东师大那帮诗人已经被主流接受,经常发表作品,而孟浪、默默这帮人远离主流诗坛,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江湖化。实际上我也是这种状态,跟孟浪这帮人,四川这帮人,包括郭力家这帮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共鸣,或者是臭味相投。大家都在社会底层,远离主流社会,甚至都不在国营单位,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都处在边缘化,所以当时跟这些人交往是最多的。说白了,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主要是这些人的展,就是大家没有找到主流的平台,生存方式也都处于边缘化,加剧了强烈表达自己诗歌主张的阶段。至于官方的邀请,唯一一次是在1987年,黑龙江省**找我去参加一个青年诗歌研讨会。省**发给我一个申请之类的表,他们不清楚我的骨子里对官方组织和主流诗坛是不屑的,我居然做了一个特别极端的行动,当着人家的面把那个神情表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了,现在想来确实有点过分了。
苏:这也说明一种态度,就是你坚持的原则和坚守的立场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偏离过。你始终在讲,你写诗是为了对抗死亡和表达内心,但作品是另一回事,难道你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他,甚至获得赞誉吗?其实我想说的是,诗歌江湖也是个名利场,你到底有没有功利性的想法。
朱:我的写作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表达自己,一个是对抗死亡。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死亡一直是笼罩我头上的阴影,我们的终极就是走向死亡,这是生命中罩在头上的最大一块乌云。我觉得诗歌是我对抗死亡最直接的最有力的表达方式,那么从写作过程本身,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功利性,但是写完了以后,确实也想过发表,包括自己印制交流文稿等等。骨子里却有另外一种功利的渴望,就是想获得传世的名誉和荣耀。像唐宋时代和十九世纪的那些著名的诗人啊,确实有这种青史留名的想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现实中我对诗坛上那些功利性的奖项是抵触的。
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精神特质,我们写诗完全是忠实于自己的热爱,是生命潜能的冲动,说到底,不仅与奖项无关,和所谓的诗坛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接着谈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划分自己的写作时期你会怎么划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