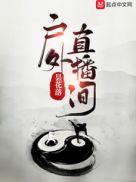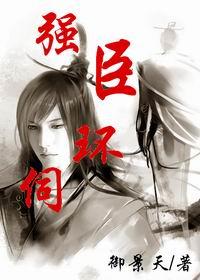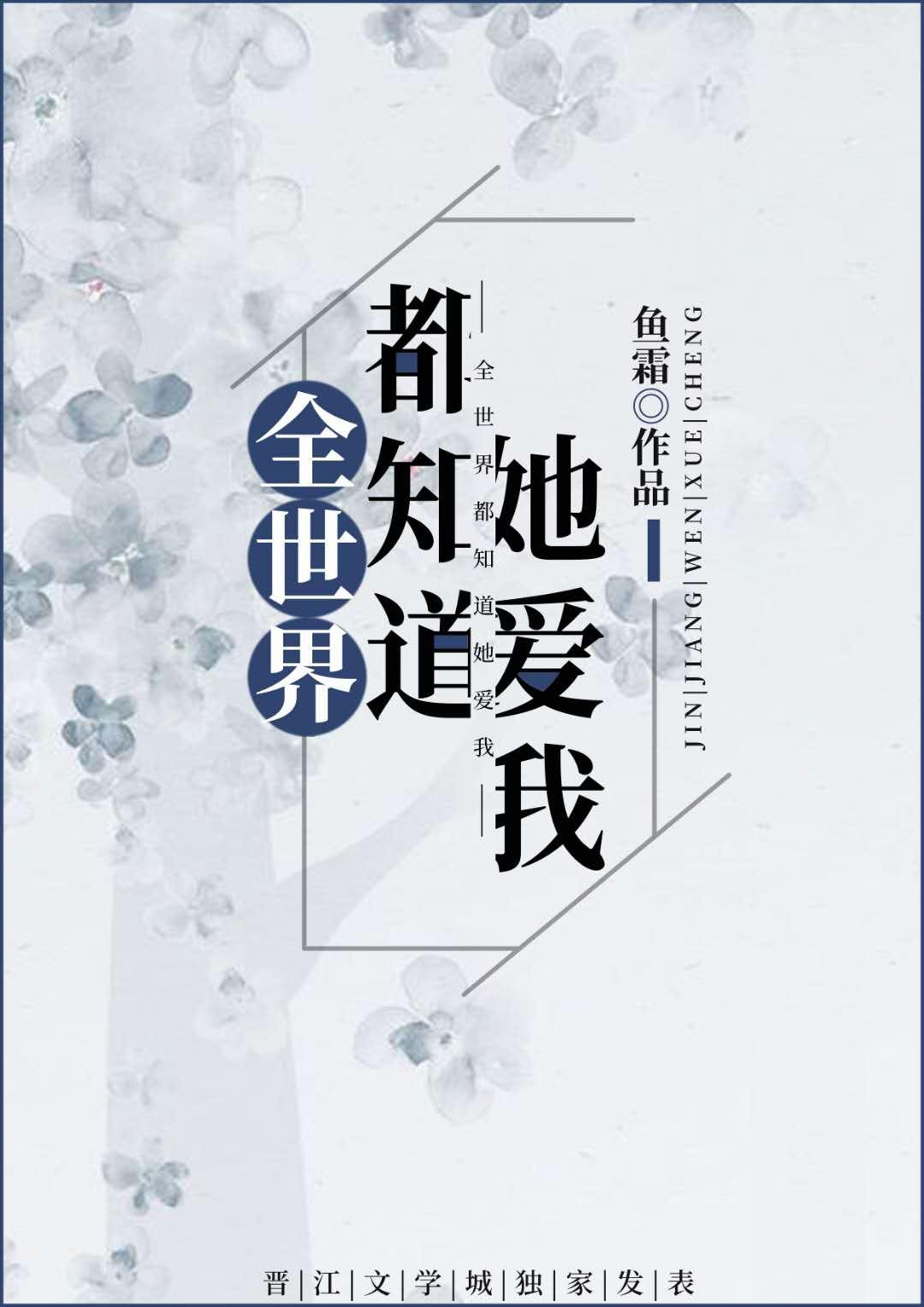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快婿 > 123杀人唇舌(第1页)
123杀人唇舌(第1页)
秋夜微凉,洛阳城里灯火一片,熙熙攘攘。
这座神京城,帝国心脏,已经废除宵禁五十余年,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在此交汇谋生。
这里的风吹草动,都会沿着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如血液在血管中奔流般持续影响全国。
今夜看似平静,实则水面之下暗流涌动。
大相国寺南,隐约能听到几声犬吠,长辈吆喝孩子的声音,孩子啼哭。
吴光启叹口气,焦急在院中踱步。
妻子和孙女在一旁为他煮茶。
孙女脸上的焦急已难以掩饰。
女大不中留。。。。。。
他缓缓放下手中信封:“赵立宽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
“他在信里说了什么?”孙女忍不住问。
他把信递给孙女,这不是什么不能看的东西。
那小子在信里没写什么前线战况,没写遇到的困难,只写了他遇到的那些西南百姓的艰苦处境。
大片荒芜糟蹋的田地,人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家人尽散遇到军队就求死的老人,奶奶带着孙女每天晚上偷摸在战场捡食尸体为生,不少灾民卖儿卖女,叛军屠城杀人,尸横遍野。。。。。。
并说要结束这些不彻底战胜叛军是不可能的,所以请求自己在朝堂上支持他继续打下去。
这小子还在书信最后奉承了几句,说自宣州相遇,就看出他是个为百姓考虑的,所以只敢写信来求他。
说得什么屁话,自己可不受这奉承。
京城里三品以上能说上话的,好像除了自己他还和谁能说上话似的。
不过转念也有些感动,不管他说这话有几分真假,确实是为百姓考虑的,看得到前线百姓的艰苦。
别人说肯定不信,赵立宽这话自己却信的。
并不是自己相信那小子,而是要看他的处境,他的作为。
为官几十年,一步步爬到宰相的位置,早明白官场上的道理,不要看别人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嘴上的话不牢靠,实际做的才算真。
如今赵立宽处在那样的位置,他只要抽身而退,必是功成名就。
四品的左卫上将军还能往上,以他功劳回来至少也是个殿前指挥使、副指挥使,或是兵部侍郎的位置。
他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任何官场上的人都不会像他一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