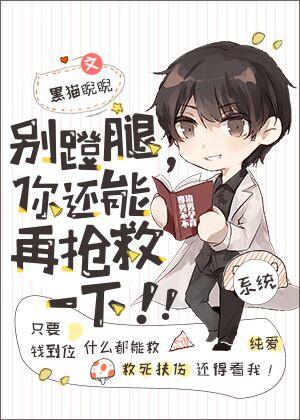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恃宠行凶(复仇) > 战后(第3页)
战后(第3页)
“胡说!”
江月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蒙着面,直等他开口唤她,才试探性地放下了手掌。
他立在她身后,一身鸦青色衣衫松松垮垮罩着,遮盖住了大部分伤口的痕迹,看起来少了些战场杀伐的凛冽,却多了更明显的疲惫。
那身染血的、沉甸甸的铁甲堆在角落阴影里,无声无息。
“吃点东西。”定山和溯风提着两个食盒进来,低声招呼。
食盒掀开,里面是几个粗面窝窝头,一大碗熬得稀烂的肉粥,还冒着热气,旁边一小碟黑乎乎的咸菜。
简陋粗糙,但对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厮杀的人来说,有着朴素的吸引力。
“就这些粮,还是从郡守府借的。对,就柳如是的爹——柳章那儿借的。”
“雁门关缺粮短食的困局,什么时候才能解啊。”
“不说了,主子,初霁,你们先吃,吃完好好休息。”兄弟俩带上了门。
谢徵玄沉默地坐下。江月见把肉粥推到他面前,又拿起一个窝窝头掰开,递给他一半。
两人就着这昏黄的油灯,默默地开始吃。屋子里只剩下轻微的咀嚼声和陶勺碰到碗边的脆响。
江月见吃得慢,不时抬眼看看谢徵玄。他吃得很专心,动作有力。
“匈奴是不是彻底退了?”
谢徵玄点了下头,“匈奴主力这一次伤得太重,马都惊跑了七成。没马,他们就跳不高了。”
“至少这个冬天,”江月见的声音稍微提了提,似乎想让语气更肯定些,“雁门关这边,能喘口气了。”
“嗯。”谢徵玄放下了勺子,碗里的粥已经见底。他脸上的灰败和先前那种沉重的恍惚似乎随着这顿热饭下肚,褪去了一些,眼神有了焦点,虽然深不见底,但至少落在了当下。
他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收拾完残局,清点完缴获,大军休整几天。”
“好,方才疯刀已经带领容羡去了。他担着监军之职,又领着虎符,这些操心的事,就让他去做吧。你好好休息几天。”
谢徵玄颔首,“好。听你的。”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捏紧了那个吃了小半的窝窝头。
“那……骠骑将军的案子……”她开口。
他的目光迎上她的视线,一股又酸又涩的热意猛地冲上鼻梁,她瞒着那个足以让她再死一次的秘密,每每称呼她的父兄,却只能称其职位,故作生分。
“我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明天晨起,就去查。”
江月见用力眨了眨眼,才把那不争气的水汽逼回去。她没说什么谢谢,只是重重地点了下头,用力咬了一口手里快被捏变形的窝窝头,咀嚼着那干涩粗糙的滋味,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
“最紧要的,”谢徵玄的声音沉稳地接上,“要先找到当年那个指控江颀风于粮仓纵火的人,那个告密的长史。
他说他亲眼目睹江颀风纵火。火起了,只有他看到他从里面跑出来?是他当时跳出来嚷嚷开的,对吧?”
“没错。就是他,那个姓沈的长史沈遂——说起来,他还是江颀风的表舅。”江月见的语速瞬间快了起来,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愤然。
“沈遂……好一个大义灭亲。呵。”谢徴玄冷笑。

![[综英美]别催,天使兽在进化了](/img/2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