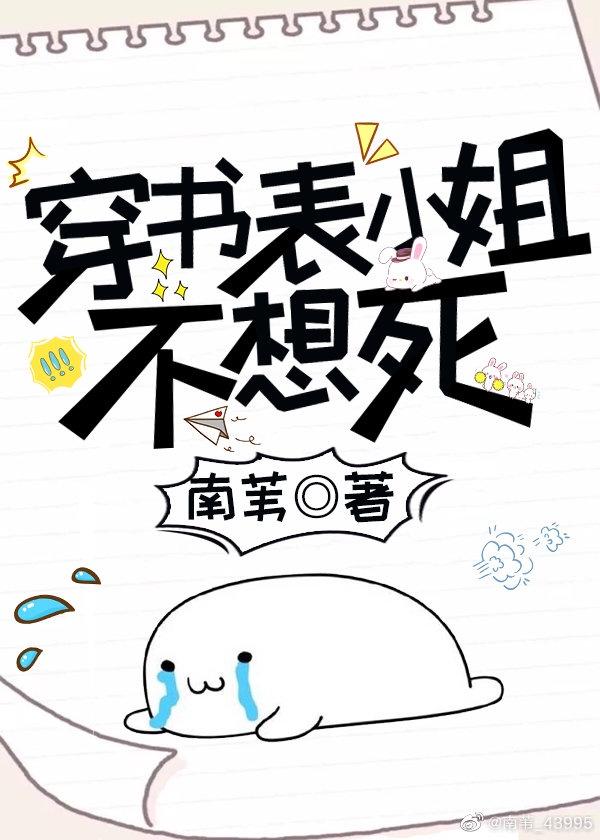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假千金和真少爷在一起了 > 2430(第22页)
2430(第22页)
嗯。
程明簌从她嘴里套话不费一丝工夫,看来是认识了。
不仅认识,可能还关系不一般。
程明簌对齐韫此人没什么印象,知道是这次的会试榜第一,同窗们曾经谈起过他。
齐韫的父亲只是举人,才学一般,能力更是平庸,先帝年间在兰阳县任知县一职,在任期间河道决口,淹没大量农田村庄,死伤数百人。齐父虽带官兵竭力抢险,但因前任知县留下的堤坝基础不牢,加上连日暴雨,终酿成大灾,齐父也因办事不力被下狱。
虽然说他也挺冤的,不过既然为一方父母官,有时候,庸碌也是一种罪。
这种公罪不会牵连子孙,所以齐韫才可以继续参加科考。
“原来不认识吗?”程明簌轻笑一声,他站了起来,垂首,嘴角凝着笑,状似随口闲谈,“说起来,我还与那位齐郎君见过一面,不过没说得上话,当真芝兰玉树,先生说,他才华横溢,等到殿试时,状元应当也非他莫属了,哎,前程似锦,官途坦荡,真叫人羡慕,倘若有幸能结识就好了。”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齐韫,也不感兴趣,程明簌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前世,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举子中,并没有叫齐韫的人。
大概这一世改变了许多东西,命轨与从前有了偏离,许多人的命运都已经不同了。
程明簌脸上露出可惜的表情,薛瑛一听什么,前程似锦,官途坦荡,还能考状元,脸色比之前更难看了,嘴唇嗫嚅,伤心之情溢于言表。
怎么会这样,若早知齐韫这么厉害,她就不躲着他了,也不将话说得那么狠心。
长得好,有学问,能当大官,让她长面子,她先前想嫁的就是这种人,如果不是因为徐星涯吓唬她,说齐韫是罪臣之子,想借侯府的东风让自己平步青云,薛瑛就不会翻脸不认人了。
都怪徐星涯,想了想,又觉得程明簌也不是好人,都怪他们。
薛瑛越想越委屈,翻身躺在榻上,将脸埋进枕头里,“呜呜……”
程明簌问道:“怎么了?”
她不理他,他越问,她越伤心,用被子将自己包成一个蚕蛹。
“好端端地你哭什么?”
她的情绪一向来得这么快,让人捉摸不透,程明簌问了几句她都没有回应,他便凑到榻边,伸手去拉被子。
“你别管我了。”薛瑛闷闷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可怜兮兮地说:“我好难过,我要自己呆一会儿呜呜。”
“你先出来。”程明簌继续拉被子,她把自己包得很紧,拉都拉不动,“出来说。”
“你不懂。”薛瑛难过死了,眼泪滚滚而落,肠子都要悔青。
程明簌:“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就懂了。”
薛瑛根本不理他,哭得都要喘不过气。
好后悔好后悔。
好日子飞走了。
怕她在里面把自己闷死了,程明簌手上用了点力,薛瑛的头露了出来,她脸颊被闷得发红,几缕乌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和腮边,长睫被泪水打湿,唇上精心涂抹的胭脂早已晕染开,在白皙的肌肤上拖曳出几道暧昧的嫣红水痕,平添了几分脆弱又狼狈的艳丽。
察觉到被子被掀开,自己狼狈的样子被程明簌瞧见了,她回头,脸上露出慌乱与羞恼的神色,瞪了他一眼,想要重新将自己埋起来。
程明簌紧紧拉着被子,语气不容置喙,“不准躲,要哭出来哭,在里面闷死了算谁的。”
薛瑛本来就伤心,偏偏自己还摊上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夫君,越发觉得自己命苦。
程明簌将榻上的锦被捧了起来,先丢到一旁的小榻上去。
回来时手上多了一杯水,递给她,“喝口水,润润嗓子再哭。省得哭哑了,明日你爹娘还以为我怎么欺负你了。”
薛瑛抽抽搭搭地抬起泪眼,看了看那杯水,又看了看程明簌没什么表情,但线条冷硬的脸,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伸出手,捧起杯子,小口小口地啜饮起来。
程明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等她喝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地开口,一针见血:“怎么,哭成这样,是喜欢那个齐韫?”
他早已看穿前因后果。他的这位好夫人,在被迫嫁给他之前,显然也没闲着,四处物色着能配得上她的如意郎君,结果却因为担心齐韫罪臣之子的身份牵连到她,把眼看着要飞黄腾达的状元郎当碍事的石头一样踢开了。
这样的人说不定有好几个,薛瑛在外面欠了一屁股风流债,估计她自己都算不过来。
眼下齐韫高中,风光无限,她便开始悔不当初,跑到他面前哭天抢地。
薛瑛捧着杯子,吸一吸鼻子,思考他的话,喜欢吗?好像也没有,她就是有些不甘心到嘴的鸭子飞了。
“我的状元夫人……呜呜……我的诰命……没了……都飞了……”
她可惜自己错失如意郎君,阴沟里翻船,嫁给程明簌这个没用的男人,还总是受他威胁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