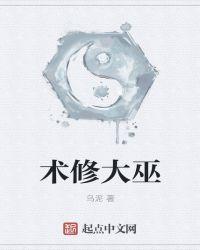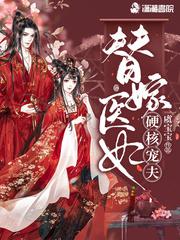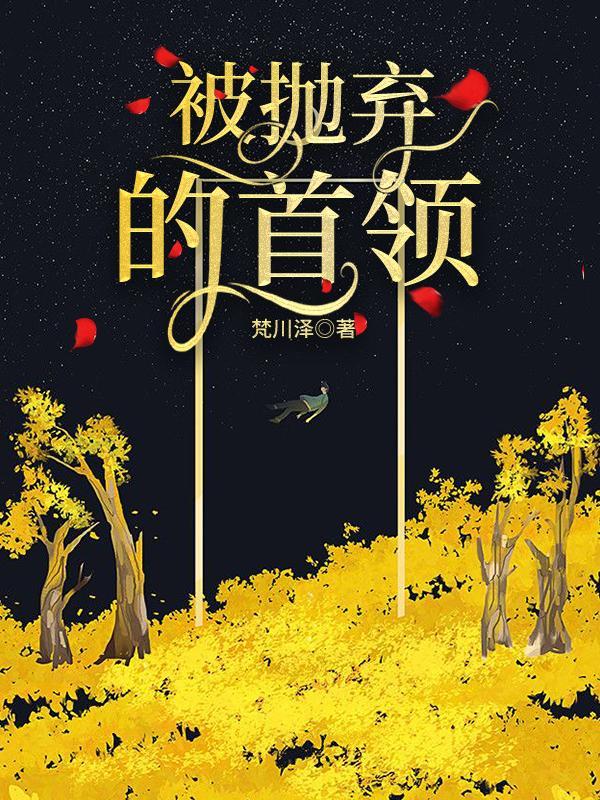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黎民日报 > 清明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2页)
清明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2页)
一个小厮快步走来通报道:“老爷,夫人,车马已经备好了,你们现在出发吗?”
“嗯。”孟允抒放下杯盏看向许昭,“我们走吧。”
她已经给秋盈留过口信,告诉她自己往返大概需要八日。不用说她也放心,在这段时间内秋盈肯定会打理好报社,出不了半点差错。
孟允抒率先上了车,伸出双手接应许昭:“小荷,来。”
“爹爹等一下。”小荷走到马车前,却制止了许昭抱她的动作。她小心地在自己袖中的口袋里摸了一阵,让车夫张开手心,这才肯松开自己的拳头。
她挪开手,仰起小脸对车夫笑道:“吴叔叔,这是给您的。”
车夫看着那两个已经有些融化发粘的糖块,笑得合不拢嘴:“谢谢小荷,叔叔保证让你坐得舒舒服服的,早些到绥宁。”
孟允抒早就发现,小荷的心思活络,脑子里面的主意也多,即使是她和许昭从来没有教给她的东西,小荷也能无师自通。这让孟允抒省了不少心,可同时她也不大容易揣测小荷的真实想法。
她把目光落到了小荷怀里的那个匣子上。
孟允抒和许昭将小荷夹在中间,她则把那个匣子紧紧抱在怀里,显得这个匣子才像是他们当中最重要的那个。
先前她和许昭曾多次询问小荷,这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可小荷的口风实在太紧,始终不肯告诉他们答案。在孟允抒的旁敲侧击屡次被她识破之后,为防止她们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孟允抒只好就此罢休。
她看向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心想,小荷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己的秘密,真不知道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们奔波了一天一夜,终于抵达了绥宁。在处理过一些琐事后,第三日上午,孟允抒和许昭一同前往他们计划内的目的地——开在绥宁县的黎民报社。
十五年过去,得益于各项新政的实施,绥宁县已经一改先前灰头土脸、穷山恶水的模样,街上的行人穿起了时兴的衣服,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
孟允抒抬头确认了一下题写着“黎民报社”四个大字的匾额,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带着许昭和小荷大步流星地走进报社,对柜台后的那名女子笑道:“陈掌柜,你还认得出我吗?”
那掌柜闻声抬头,她愣怔片刻,脸上忽而现出惊喜的神色。
“允抒!”她激动地叫起来,扔下算盘跑来与她紧紧相拥,泪水很快便夺眶而出。
终于,她咽下喉头的兴奋分开二人,抹了一把眼泪,端详着孟允抒的面庞。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九年前。和那时相比,你完全没有变化。”
这陈掌柜正是陈玉宛。当年她和金婕在孟允抒的报社先行实习,后来又通过了考核,成为黎民报社的正式员工。在其后的几年中,金婕萌生了返回故乡的念头,于是找到孟允抒商议此事。最后,在孟允抒的帮助下,金婕回到绥宁开起了黎民报社的分社,而陈玉宛本就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因此索性随她一起来到绥宁,帮她打理生意。
孟允抒对陈玉宛笑道:“姐姐也和过去一样,还是那般容色倾城。”
“什么容色倾城,我的一双儿女都那么大了,我也人老珠黄了。”
陈玉宛自嘲着,她和孟允抒闲聊一会,这才注意到她背景中的许昭和小荷。
“不知许大人前来,我有失远迎,实在抱歉,还请您见谅。”她连忙给许昭行了礼,而后看了眼小荷问道,“这是不是……”
“对。”孟允抒肯定了她的猜测,“她是我女儿。”
小荷和许昭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旁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
“小荷,过来。”孟允抒牵着小荷的手,向她介绍陈玉宛的身份,“这就是娘亲给你讲过的那位陈姨。”
小荷笑容明媚,落落大方地向陈玉宛行礼:“陈姨好。”
陈玉宛听到那个耳熟的名字,迟疑着问孟允抒:“她叫小荷?”
孟允抒的语气坚定:“嗯,乳名小荷。”
陈玉宛的眼波微动,她俯身看向小荷,温柔地摸摸她的发顶,像是在亲昵地问候一位故人。
“小荷,你今年几岁了?”
小荷欢快地回答道:“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