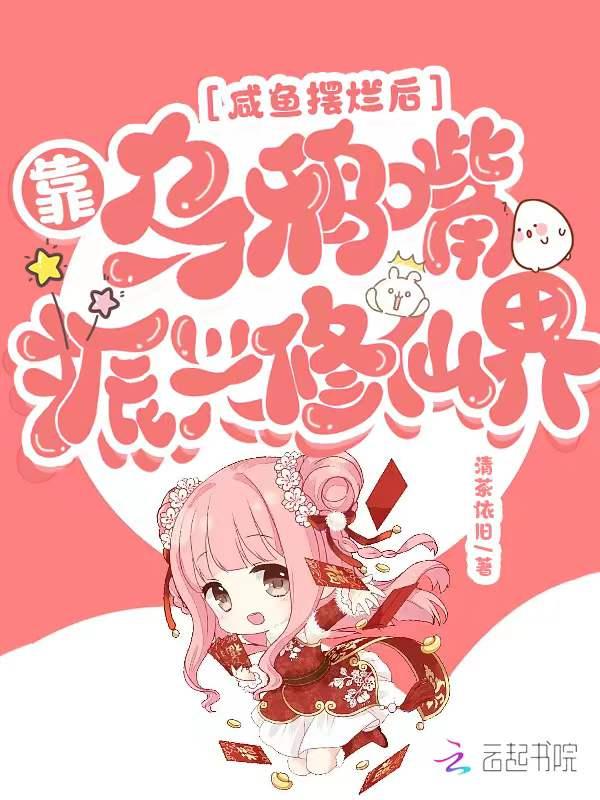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情迷1942(二战德国) > 研讨(第2页)
研讨(第2页)
谁都知道,Le
Patissier是巴黎最昂贵的甜品店,一块蛋糕的价格,都顶得上普通人家半个月的面包配额了,他真是来送蛋糕的?她不大信。
叁天了,从那夜到现在,她努力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的作息,按时开诊,假装一切日常,但假装终归是假装,就连梦里,她都会看见君舍带着一群人来抓自己,冰冷的枪口对准自己,那画面真实得让她每次都能惊醒。
女孩指尖陷进掌心里去,汲取着那一点痛意带来的镇定。“谢谢,可是我最近在…。”
“最近在控制糖分?”男人自顾自接过话头,他解开缎带,蓬松如雪的蛋白霜,裱成螺旋花样的棕色奶油,甜香飘出来,盒子里俨然是个栗子蛋糕。
“那就当是……慰劳我这个不请自来的病人?”他指了指自己的手臂,“来复查一下,文医生总不会拒绝吧?”
俞琬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个长狗鼻子的人是如何在她眼前划伤了手。
可从那天到现在,都整整过去了两个多星期,那伤口大可能也都长好了。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显然不像是真为了伤。这么一想,心头便越发七上八下起来。
她垂下眼,过了片刻才轻轻点了点头。
戴上手套,女孩指尖落在那新疤上,淡粉色,指腹按压,皮下的组织弹性良好,无粘连,几乎算得上一个教科书式的愈合案例了。
俞琬专注检查那伤疤,全然不知君舍的目光正肆无忌惮舔舐在她脸上。从她紧抿的唇瓣,到蹙起的眉尖,连她睫毛颤动的弧度,都被他一一捕捉,
此时,阳光穿过百叶窗,漏下的光束恰好照在她脖颈上,那里皮肤很薄,青色血管隐约可见。
一瞬间,某种暴戾的冲动窜上来。他控制不住地想,用指尖贴上那片皮肤,感受她的脉搏是真的如表面般平稳,还是早已在自己的注视下乱了节拍。
“恢复得很好。”温温软软的声音打断了这危险联想,女孩抽回手来。
“是吗?”男人慢条斯理地卷下袖管。“可我总觉得,这里有时候,还会隐隐作痛。”
女孩不自觉蹙了蹙眉。都过了那么多天,他是真的疼,还是在指别的什么?
和君舍打交道像是在走钢丝,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的警惕来,思索了片刻才敢开口。“不用担心、可能是神经末梢恢复期的正常反应。”想了想,又加了句。“我可以给上校开点促进愈合的药。”
“呵。”棕发男人低笑一声,听不出是喜是怒,空气就这么静了一瞬,女孩疑惑抬眼,便撞上他嘴角那抹弧度,神经倏然就绷紧了。
那笑,她太熟悉了,每次他这那样笑,接下来都没不会有好事。
“文医生说得对,或许是我多虑了,”他话锋一转。“其实今天来…除了复查,主要是想寻求一点专业意见。”
棕发男人慢悠悠顿了顿,“如果我想让一个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但又不想立刻致命,从背后下手,哪个位置最合适?”
轰——
俞琬的脑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写着处方的手几不可察地一抖,墨水悄悄洇开来。
背后,失去行动能力…。他为什么问这个,他指的是谁,一个想要下手的新目标,还是又在试探她?
她的指尖微微发起颤来,却在下一刻不动声色把钢笔握得更紧了些——金属笔杆硌进掌心,仿佛这是唯一能让她稳住心神的武器似的。
难道他在说伊藤,不,伊藤是正面被刺的,但颈后确实是让他失去行动能力的致命伤。又或者,君舍从日本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他重新开始查那个案子了,所以用这种话来套她?可他说的是“从背后”,是不是并没真正查清楚?
不能慌,他是盖世太保,问这种问题可能有无数种原因,不一定就是针对她…不一定。
女孩强迫自己把视线从处方笺上的墨点移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