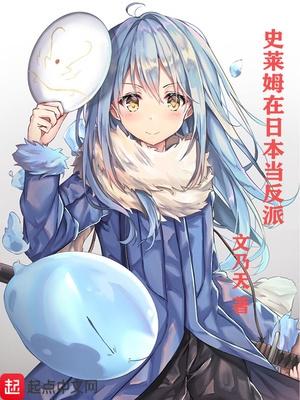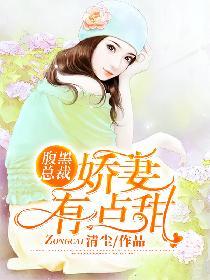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宋文豪 > 第245章 教其为丧髽之法当卑小(第2页)
第245章 教其为丧髽之法当卑小(第2页)
程颢见此盛况,心中欣慰,对程颐道:“陆子之名,已非止于文坛,而是渐入仕途。他若能持此志,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动,便可真正以文载道。”
程颐冷哼一声:“只怕他入仕之后,便不再是昔日之陆北顾。”
程颢摇头:“若他真能以文辅政,以道济世,即便身处庙堂,亦不失其志。”
国子监外,士子们议论纷纷,皆在猜测陆北顾的前程。
“陆兄若真入翰林院,那便是天子近臣了。”一人道。
“若能入翰林,将来入阁拜相,亦非不可能。”另一人感叹。
“可惜啊,仕途险恶,人心难测。陆兄若真入朝,怕是免不了卷入党争。”又一人忧心忡忡。
而在国子监后院的亭中,陆北顾与闵欣、宋堂等人围坐,正谈论此事。
“陆兄,你可知,如今京师已有不少人将你视作新进之才,甚至有人议论你将来可入阁拜相。”闵欣道。
“此事我亦有所耳闻。”陆北顾淡淡一笑,“然我心中所念,仍是文道之正,非仕途之显。”
宋堂点头:“陆兄有此志,实为难得。”
陆北顾望向远方,缓缓道:“文者,载道之器也。若不能以文辅政,以道济世,则文亦无用。我愿以己之所学,为国所用,为民所依。若能以此为志,纵使仕途险恶,我亦无所畏惧。”
众人闻言,皆肃然起敬。
夜深人静,陆北顾独坐书房,提笔写下:
“文者,载道之器也。若不能以文辅政,以文济世,则文亦无用。今得礼部垂青,愿以己之所学,为国所用。”
他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思绪万千。
他明白,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而他,已准备好,以文载道,以笔为剑,书写属于自己的时代。
陆北顾自礼部归来,国子监内士子议论纷纷,皆对他此次参与策论命题之事议论不休。有人敬佩,称其才学出众,得礼部重用;亦有人暗中讥讽,谓其锋芒太露,恐遭人忌。
“陆兄此番入礼部,可谓一步登天。”一位士子在藏书楼低声对同伴道,“听说李尚书有意荐他入翰林院,若真如此,陆兄便是天子近臣了。”
“然则仕途险恶,人心叵测。”另一人叹息,“陆兄若入朝堂,恐难独善其身。”
“可若不入仕,如何以文载道?”第三人反驳,“陆兄既有此志,便当一试。”
陆北顾听闻此言,只是淡然一笑,并未多言。他深知,自己虽得礼部赏识,但朝堂之上,非单凭才学便可立足。他尚年轻,若贸然入仕,恐难立足。
然而,礼部的召令却比他预料的更快到来。
三日后,礼部尚书李大人再度召见陆北顾,命其参与“省试策题审阅”之事。此次省试,礼部拟从各地贡生所呈策文中择优录取,以备明年正式省试之参考。陆北顾被委以重任,与翰林院诸学士一同审阅策文,评定优劣。
“陆子。”李尚书亲自召见他,神色凝重,“此次策文审阅,关乎明年省试之方向。你须得公正无私,以才取人,不可因私情而偏废。”
“学生明白。”陆北顾拱手应道。
“你虽年少,然才学出众,已得诸公认可。”李尚书目光深沉,“此次审阅,亦是对你才识与心志的考验。若能公正无私,将来仕途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