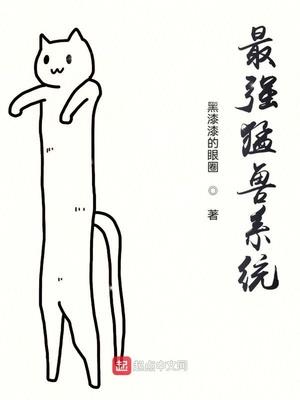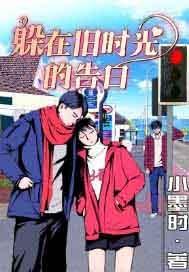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唐协律郎 > 0462 分胙不公(第2页)
0462 分胙不公(第2页)
“听我说。”张岱压低声音,“书还是要编,但内容要做调整。去掉所有涉及古乐考据的部分,专注科举策论、诗赋格式、时务见解。封面也不署你名,改为‘京兆士林辑录’。资金方面,我会通过康立德的车马行走账,确保不留痕迹。至于印刷??”他顿了顿,“你去找赵氏印坊老板,告诉他,协律郎愿以三百贯预付订金,条件是必须在十日内完工,且不得泄露半个字。”
顾兴竹呼吸急促起来:“协律郎……您这是要公然对抗那些势力?”
“不是对抗,是布局。”张岱目光幽深,“我要让他们看到,我不仅有能力庇护你们,还能反过来掌控舆论流向。三百贯买不了多少兵马,但足以掀起一场文坛风暴。等这本书在春闱前流入各大书院,天下士子都会知道,有个协律郎在默默支持寒门出路。”
顾兴竹久久不能言语,终是深深一拜:“顾某愿追随协律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午后,张岱接到宫中传召,命其即刻赴延英殿觐见。他整衣束带,随内侍入宫。途中经过含元殿侧廊,忽见一道熟悉身影立于丹墀之下,披甲执戟,正是张淑。
“阿叔?”张岱轻唤。
张淑回头,眼神复杂:“宗之,小心说话。陛下今日召你,恐非仅为乐事。”
张岱心头一紧:“可是出了什么事?”
“渤海公昨夜上表,弹劾太常寺近年修乐失度,致使郊庙祭祀用乐不合古制,有亵渎宗庙之嫌。矛头直指协律郎空占其位,不务实务,专事结党营私。圣上未置可否,但令你今日奏对。”
张岱冷笑:“果然来了。”
进入延英殿时,皇帝正倚坐御榻批阅奏章,面容倦怠。张岱行礼毕,皇帝抬眼看他,淡淡道:“听说你最近很忙?家宴、交友、荐书、租车敛财……朕听说,连北坊妓馆都在传唱你写的曲子?”
“回陛下,”张岱坦然道,“臣确曾参与族人家宴,亦与同僚聚会饮酒,然皆私谊往来,未曾废公。至于荐书一事,实为鼓励寒门士子勤学进取,非为私利。臣掌协律之职,本当以雅乐教化天下,然今科举重诗赋而轻礼乐,致使士子不知五音之义,不解八音之器。臣欲借通俗曲调传播乐理知识,使百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此亦不失为教化之一途。”
皇帝眯起眼睛:“所以你是说,你在用花街柳巷的歌声来推行礼乐?”
“正是。”张岱毫不退缩,“昔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然韶乐高妙,非人人可解。今之世,民心思变,若一味拘泥古法,反致礼崩乐坏。不如因势利导,以俗入雅,由浅及深。臣所作小曲,皆合宫商角徵羽,暗藏十二律吕之序,孩童传唱之际,已在无形中学得音律根基。待其长大,自然亲近雅乐。”
殿内一片寂静。良久,皇帝缓缓点头:“有趣。那你可敢当场奏一曲,让朕听听,这‘教化之音’究竟如何?”
张岱起身离席,从袖中取出一支紫竹短笛,躬身道:“臣请奏《清平调?春晓》。”
笛声乍起,如溪流潺潺,穿林拂叶。旋律初极简朴,仅用宫、商二音来回呼应,继而角音加入,如鸟鸣山涧,生机盎然。随后徵羽递进,节奏渐快,仿若晨光破雾,万物苏醒。整曲无一字歌词,却令人仿佛看见春日黎明,花开满园,童子嬉戏,农夫荷锄归田。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
皇帝久久不语,终是叹道:“此曲虽简,却有天地清明之象。比那些冗长繁琐的雅乐,反倒更近人心。”
张岱伏地叩首:“陛下明察。礼乐之道,贵在通达人心,不在繁文缛节。若能使千万庶民因一首小调而知音律之美,则胜过千篇雅奏。”
“罢了。”皇帝挥袖,“渤海公之奏,朕不予采纳。尔当恪尽职守,勿负朕望。”
退出大殿时,张淑已在门外等候。见张岱出来,急忙迎上:“如何?”
“没事了。”张岱微笑,“而且,我猜很快就会有人主动来找我合作。”
果然,当日晚间,宫中传出消息:皇帝特旨,命协律郎张岱主持编撰《大唐新声集》,收录当代优秀词曲,颁行天下,作为民间乐舞标准。此举名义上是为了振兴礼乐,实则是皇帝借张岱之手,平衡北门军事集团对文化领域的渗透。
消息传开,朝野震动。
三日后,卢崇义亲自登门拜访,态度谦恭,言称愿助协律郎搜集各地民谣,共建文化盛举。张岱欣然接纳,并当即委任其为“采风使”,统领十道巡查队伍。
与此同时,顾兴竹主编的《京兆士林辑录》如期刊印,五千册书籍迅速流入东西两市书肆,引发士林热议。书中不仅系统整理了科举应试技巧,更隐晦批评了门阀垄断仕途的现象,被众多寒门学子奉为“指南宝典”。
张岱站在自家院中,望着夜空繁星,轻声道:“风,终于吹起来了。”
他知道,这场博弈远未结束。北门仍有杀机潜伏,公主府暗流涌动,朝廷党争日益激烈。但他已不再畏惧。因为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刀剑,而在人心。只要他能让更多人听见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哪怕是最微弱的笛音,也能穿透重重宫墙,响彻长安城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