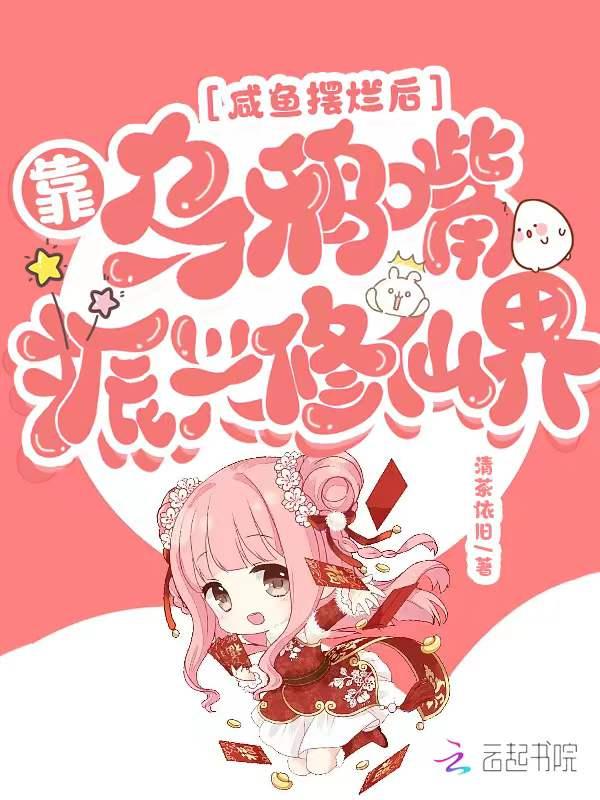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我在古代锔瓷暴富 > 136(第2页)
136(第2页)
“莫二爷,这里交给我。惊春小姐,没事了。”
冲着莫失让和莫惊春拱拱手,沈六沉声说道。
危机解除,莫失让紧绷的神经一松,居然浑身失力一般的后退好几步,如果不是有柜台抵着,可能他就要摔倒在地了。
“爹!”
莫惊春惊呼一声,匕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冲过去扶住莫失俭,而另一边,早有莫问月搀扶。
“三哥,都怪我,都怪我!”
莫问月红着眼眶道。
“老姑,一家人不说这个,你和先我扶着我爹去坐下,陈叔,麻烦您派个麻利的赶忙去请郎中。”
老陈是莫惊春他们家新请的账房,之前是在府城做事,但他老家是浮梁。因如今父母身体多病,而府城开销也大,故而才想着回浮梁找活干。正好莫家要雇人,双方一拍即合,敲定了雇佣关系。
“二小姐,我已经让小李子和小邓子去了,此外,我也让他们顺便报官。”
老陈一边帮着莫惊春、莫问月让莫失俭坐下,一边回道。
莫惊春点点头,对老陈的做法很满意。
“郎中来了!都让让!”
“慢点,慢点,老身这骨头经不住啊!”
车马声从门口穿过,不过须臾,小李子拽着须发皆白的老者冲了进来。。。。。。
没过多久,县衙的衙役也到了。
尽管最后瘦高个那几个泼皮都被带下去打了板子,但几人嘴倒是紧,死活不认是被人指使。
经此一闹,续物山房是再也开不下去了。三日后,莫失让便红着眼眶,亲手摘下了门口的牌匾,大门紧闭,上了沉重的门栓。
曾经承载着莫家三房希望,也是看着莫惊春一家如何成长的老铺子,在流言与恶意的风暴中,被迫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门外的喧嚣似乎暂时隔绝,但门内的压抑与愤怒,却如同阴云,愈发浓重地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这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的氛围中,莫问月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让人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坚韧。
她不再流泪,也不再怨天尤人,只是将自己关在后院那间小小的瓷窑工坊里,比以往更加沉默,也更加专注地学习制瓷技艺。
拉坯、利坯、画青花……每一个步骤她都做得一丝不苟,仿佛要将所有的委屈、愤怒和不甘,都揉进那细腻的瓷土里,绘在那素白的胚胎上,再投入窑火中淬炼成坚不可摧的瓷器。
那双原本只执绣花针的手,如今常常沾满泥浆,甚至磨出了水泡,她却浑不在意,眼神里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定。
莫问月明白,言语无力,唯有自身立得住,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才是对一切诽谤最有力的回击。
看着这样的莫问月,不止是莫失让和其他的莫家人,就是莫惊春都惊叹不已。莫忘夏甚至还主动提起曾经在自己的那场可笑“添妆宴”上莫问月说的话。
“老姑,如今看来,你是大智若愚啊!”莫忘夏撞撞莫问月的肩膀,笑着说。
莫问月惭愧的笑笑:“是我无知,是我蠢才是,忘夏,谢谢你不与我计较。。。。。。”
物是人非,果然真正让一个人成长的往往不是忠言逆耳,而是真真实实的挫折与磨难。曾经的她,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被爹娘宠爱,被众人不论好坏的夸赞,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不知世间险恶。
一场变故,让她从云端跌落谷底,流言蜚语如刀割般刺痛她的心,可也正是这一切,让她如梦初醒。
时近黄昏,残阳如血,将浮梁县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染上一层凄艳的橙红。
几匹快马踏着暮色,蹄声急促如擂战鼓,打破了浮梁晴釉巷傍晚的宁静,径直冲向城西莫家三房那座略显僻静的院落。